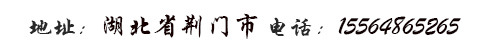枫露茶被甄嬛传抄错的作业
|
花粉们好,今天转发一篇暜航老师的稿子,《甄嬛传》与《红楼梦》相比较,有点新意,希望你也喜欢这篇文章。另外,我去年接了本城市史的小书正在收尾阶段,拖的时间不短了,deadline近在眼前,这一段集中精力完成它,也算了一桩心事,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大活儿要完成........最近想和你们分享的东西太多了,但手头任务实在不轻,请大家为我加油吧!另外,疫情汹涌,大家做好防护,愿我们都健康平安。BY百合 《红楼梦》是曹公“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写成的文学巨著,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原著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堪称百科全书式的文学作品。《红楼梦》是博大精深的,其中提到的事物,有些至今仍难以参透。当代的影视剧纷纷“致敬”《红楼梦》,但涉及书中文化内容时,常出现种种纰漏,不免贻笑大方。比如,《红楼梦》中曾提到一种茶,名曰“枫露茶”。宫斗剧《甄嬛传》曾借鉴了这款茶的名称,用于剧情之中。但细细品来,剧中的“致敬”曲解了曹公的文字,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甄嬛传》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甄嬛一同入宫的闺蜜安陵容,受到皇帝宠爱。名为宫女,实为甄嬛庶出妹妹的浣碧,出于嫉妒,对安陵容恶语相向。甄嬛知晓陵容心思细密,便有意将浣碧支开,说了一句台词——“外头有刚沏的枫露茶,已经出了三四遍色了。”红迷朋友一看便知,这显然是借鉴了《红楼梦》。可是,细想一下,这台词是不是有点不对“味”呢?“枫露茶”,出自《红楼梦》第八回。这一回中,贾宝玉、林黛玉到梨香院看望宝钗,薛姨妈招待他们,品佳肴,佐美酒。宝玉兴尽而归,回到自己房中,忽然想起那一杯“枫露茶”,便让丫鬟茜雪端来品饮。谁知,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已喝了那杯茶。宝玉极为扫兴,借着酒劲大发雷霆,砸了杯子,茶泼了茜雪一裙子,并且声称要把李嬷嬷撵出去。当然,这段故事的结局烟云模糊,絮絮叨叨的李嬷嬷仍然时不时出现在宝玉的生活中,倒是茜雪,不明不白地被赶了出去。依照脂批,日后茜雪不计前嫌,在抄家后前去安慰宝玉。个中原委,引人遐想。这里且不枝蔓,只说那杯引人注目的“枫露茶”。在书中,这茶颇具特色,曹公借贾宝玉之口道来——“早起沏了一碗枫露茶,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的,这会子怎么又沏了这个来?”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实则指出了枫露茶的两个特点:一来,早上就沏好的茶,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才适合品饮,与其他茶品大相径庭。二来,多数茗茶,冲泡三至四次品尝为佳,之后味已寡淡,常需更换茶叶重新冲泡。至于妙玉所说的“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更是凡人不可企及的高雅境界。可这枫露茶不同,需要冲三到四泡,之后汤色方佳,正适合品饮。再对比《甄嬛传》中的“致敬”,可知是创作者会错了意。文本中说,早晨沏的茶,晚间正适合喝;而剧中人物说的是“刚沏的”,难道嬛嬛的枫露茶,如同咖啡一样速溶?!再者,宝玉说的是冲三四次之后,茶汤才呈现出上佳汤色;而剧中台词想效仿这一句,却偏偏说成“出了三四遍色”。想来,任是什么好茶,出三四遍色,已与废水无异,如何还能品尝?以喝剩的茶招待闺中好友,岂是待客之道?!可见,《红楼梦》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还未理解清楚文本,就急于“致敬”,套用一句歌词来说——《红楼梦》不是你想抄,想抄就能抄!不过,《红楼梦》诞生二百余年以来,让读者疑惑并争论不休的,是:这所谓的“枫露茶”,到底是什么茶?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曹公杜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谓众说纷纭。有人找到相关的文献——《本草纲目·木部》中载:“(香枫)二月有花,白色。以其花叶作露点茶,盖取其香气也。”这是说取香枫的花与嫩叶,制成枫露,用以“点茶”。具体制法,清代顾仲的《养小录·诸花露》中有载:“仿烧酒锡甑、木桶减小样,制一具,蒸诸香露。凡诸花及诸叶香者,俱可蒸露,入汤代茶,种种益人。”这种取枫露点茶的方法,是古人采用过的,但这究竟是不是《红楼梦》中所说的“枫露茶”呢?制作香露,蒸出来的必是浓稠的液体,能够快速溶于水,适合现冲现喝。对比“枫露茶”的两个特点:需要久泡;并且需要冲泡三四次,才显现汤色。很显然,这“枫露点茶”名目相似,却不可能是曹公笔下的“枫露茶”。古人向来爱茶,所谓“琴棋书画,诗酒茶花”,皆是文人墨客须臾不离的雅好。《红楼梦》中“茶香”四溢,行文颇有特色。如龙井茶,世人皆知,却只出现于后四十回续书当中。曹公写茶,偏偏有虚有实,令人无限神往。太虚幻境中纯美非常的“千红一窟”,溢出古往今来多少悲情女子的心声,但这仙界香茗,绝非碌碌尘世中人可品味;老祖宗那一钟“老君眉”,吉祥的名目令人神怡,而品种若何、口味浓淡,至今仍是众说纷纭;那众人皆觉淡,却独合黛玉的暹罗贡茶,同样似有若无,难以指实……曹公笔下的茶,向来是这样虚虚实实,仿佛那沁人心脾的茶香,萦回飘渺,却又不可触及。“枫露茶”也是同样,与其细究茶性,不如察其文理。曹公出身于江宁织造世家,少时在金陵度过,南京一带的口音特点,深深影响着他,并体现在他笔下的文字中。南京方言中,韵母in与ing不分,这是前后鼻音不分。“秦”的发音接近于“情”,“秦钟”谐音即是“情种”。另外,南京口音的声母l与n也不分,即边音与鼻音不分,因此常有人将“南京”,戏称为“蓝鲸”。刘姥姥进大观园时,无论是开宴前的诙谐话语,还是黛玉打趣的“如今才一牛耳”,书中两次将“刘”姥姥与“牛”联系起来,正因为两字发音相近。如此来看,曹公笔下的“枫露茶”,便也有了答案。提到这杯茶,正是贾宝玉发怒的前奏。曹公写出茶的名称,并非实际指向某种茗茶,而是用谐音的方法,将其命名为“逢怒茶”。贾宝玉在书中的形象一向是温文而雅的,“怡红公子”的个性,让他对女子多了几分关爱,发怒的情节,并不多见。曹公勾画宝玉发怒的场景,杜撰出“逢怒”的茶名,岂不是神来之笔。至于早起沏上、冲三四遍后品尝的细节,是曹公为了撰写情节而进行的创作。宝玉惦记多时终未能品尝,故而大怒,行文上合情合理。后文中,还有一次提到“枫露茶”,那便是祭奠晴雯的《芙蓉女儿诔》中,写道:“怡红院浊玉,谨以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四者虽微,聊以达诚申信,乃致祭于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此处以“沁芳之泉”,对“枫露之茗”。想来,“沁芳”二字虽奇,溪也罢,桥也罢,独存于曹公笔下,则“枫露茶”又何必指实?笔虚情实,岂不两妙!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erfenga.com/nefyfyl/8331.html
- 上一篇文章: 敬华春拍丨别去优衣库抢衣服啦,这股ld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