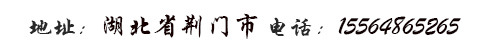崔晓新结附与提携ldquo南朱北王
|
北京治疗白癜风有哪些医院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清初名儒,有《經義考》《日下舊聞》《曝書亭集》等傳世。王士禛(—),字子真,號阮亭,山東新城人,清初著名詩人,有《帶經堂集》《池北偶談》《漁洋詩話》等傳世。朱王二人生當同時,并爲清初康熙一朝文壇名宿,向有“南朱北王”之稱。 時人及後世論及清初詩壇,多以二人并舉。最早將二人相提并論的是趙執信《談龍録》,提出可以匹敵大家王士禛者當爲秀水朱彝尊,稱“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真敵國矣”[1]而後薛雪《一瓢詩話》、杭世駿《詞科掌故録》、鄭方坤《國朝名家詩抄小傳》、楊際昌《國朝詩話》、趙翼《甌北詩話》、翁方綱《石洲詩話》、孫星衍《刑部尚書王公傳》、黄培芳《香石詩話》、尚鎔《二家詩話》、朱庭珍《筱園詩話》、丘煒萲《五百石洞天揮麈》、章炳麟《菿漢昌言》、錢仲聯《夢苕庵詩話》、徐澂《卓觀齋脞録》等皆嘗將二人并舉,且評價甚高,如鄭方坤稱“新城、長水屹然爲南北二大宗師,比於唐之李杜、宋之蘇黄,更千百年而勿之有改也”。[2] 朱彝尊、王士禛雖生在同代,成就相當,并稱朱王,但大概由於二人於人生軌迹、政治選擇以及文學理念等多方面存在較大差异,故學界對二人的交集鲜有關注。事實上,兩人有較多交往,而且在交往起初還存在着微妙的關係:二人聲望有先顯後起之别,存在着提携與結附的關係。 朱彝尊像一、王士禛、朱彝尊顯名先後之考察朱彝尊、王士禛雖以“南朱北王”并稱,然二人并非同時顯名,準確地説并非同時顯名於正統文壇。他們同爲明代望族官宦之後,但人生履歷、成名之路完全不同:王士禛少年成名,而後科舉及第,仕途平步青雲,人生順風順意;朱彝尊則是經歷了青年抗清,中年逃亡,晚年出仕的曲折歷程,名望與地位直至人生中後期才逐顯於正統政壇文界。 (一)王士禛的成名之路 王士禛生於明崇禎七年(),自幼即有神童之目,十五歲刊行有《落箋堂初稿》一集。清順治十二年()“會試中式第五十六名,未殿試而歸”[3]順治十四年()時年二十四歲的王士禛於濟南大明湖結“秋柳”詩社,即景賦《秋柳》詩四章,“大江南北和者益衆”[4],於詩壇嶄露頭角。而後次年殿試中二甲進士,順治十六年()赴任揚州推官,期間又有《秦淮雜詩》《浣溪沙》《冶春詩》等詩作,再度引發衆多文士争相唱和,聲名遠播。順治十八年()文壇領袖錢謙益序其《漁洋山人詩集》,云:“余八十昏忘,值貽上代興之日,向之鏃礪知己,用古學勸勉者,今得於身親見之。”[5]許其與己代興,將王士禛視爲文壇接班人。康熙三年()王士禛遷禮部主事,之後歷任儀制司員外郎、户部福建司郎中、翰林院侍講、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兵部督捕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入直南書房,充明史纂修官,三朝國史副總裁,官至刑部尚書,仕途平順,步步高升。而官位愈顯,聲望愈隆。趙翼點評清初吴偉業以下詩人曾云“名位聲望爲一時山斗者,莫如王阮亭”[6];李元度亦云“國家文治軼前古,扢雅揚風,巨公接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稱首”[7]。 (二)朱彝尊的成名之路 朱彝尊生於明崇禎二年(),長王士禛五歲,亦是少賦异禀,聲聞鄉里,順治九年()吴偉業游檇李,見其詩評曰“若遇賀監,定有謫仙人之目”[8]意謂假以時日,竹垞必定聲震文壇。然不久即逢鼎革之變,集國恨家仇於一身的青年朱彝尊廣泛結識抗清志士,與魏耕、祁氏兄弟等籌謀秘密抗清活動,事敗,身涉“通海案”,遠走海上避難,“屏居田野,不求自見於當世”[9],自我隱匿,放棄聞達。直至清康熙二年()清廷寬免未緝捕之“通海案”人員,朱彝尊才身獲自由。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编》卷七即曾明言朱彝尊“壯歲欲立名行,主山陰祁氏兄弟,結客共圖恢復。魏耕之獄,幾及於難,踉蹌走海上。會事解,乃赴遠游。”[10]此階段的朱彝尊多是奔走於地下,自我韜晦,并不見稱於正統文壇。之後迫於生計,“南逾五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11]開始了漫長的游幕生涯,并將生活重心轉移回文學創作、學術研究,文名又起,兼之他有意識地向正統文壇名士、清廷新贵靠近,聲望漸隆。康熙十七年()朱彝尊一改故衷,應召博學鴻儒試,出仕清廷,同年召入明史館,康熙二十一年()又入值南書房,簪珥記注,聲名大震。 (三)二人同時段聲望對比 以朱彝尊主動結識王士禛的康熙三年()爲界,王朱二人具體履歷聲望對比如下:順治十四年()王士禛以《秋柳》詩成名之際,朱彝尊正忙於結交屈大均、陳子升、萬泰、薛始亨、黎延祖、黎彭祖、張家珍、陳恭尹等明遗民;順治十五年()王士禛進士及第、次年授揚州推官,而此時朱彝尊正與祁班孫、祁理孫、魏耕等秘密商討復明大計;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元年()王士禛官運平穩,詩名大噪,被視爲新一代文埴領袖接班人,而此時朱彝尊正因清廷緝査“通海案”四處逃亡;康熙三年()王士禛先任揚州推官,旋遷禮部主事,名滿天下,而此時的朱彝尊剛從“通海案”中解脱出來,爲了生計寄人籬下,游幕四方。朱氏縱有才華學識,在相當長的時間内因政治身份、經濟原因身處邊緣,遠離主流。 可見,朱彝尊、王士禛的人生前期所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就個人聲望、地位的形成來看,王氏在前,朱氏在後,這一時期朱彝尊的地位和影響是遠不能與王士禛相匹敵的。故《四庫全書總目》所云“彝尊文章淹雅,初在布衣中已與王士禛聲價相齊”[12],是有失偏頗的。 [清]王士禛著:《王士禛全集》,齊魯書社,年二、朱彝尊結附王士禛之考論隨着滿清政權統治根基漸穩,清廷對漢族士人政策不斷調整,兼之個人窘迫經濟狀况的促發,以及傳統文士不朽情懷等多種因素共同影響作用下,朱彝尊由游幕、結附到應試、出仕,逐漸完成了政治轉向,其中结附是其立場轉變的重要一環。 (一)朱彝尊政治轉向原因之考述 以明遗民自處的朱彝尊,先是秘密抗清,拒認新朝,而後改弦更張,主動结交清廷要員,希冀對方提携自己,擴大影響,接近新朝,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 1.清廷士人政策的調整 清朝立國之後,歷順治而至康熙,政權日益鞏固,社會漸趨安寧,民間反清復明的活動眼看大勢已去。而順康以來清廷對漢族士人的政策也進行了積極調整,實施了諸多安撫争取漢族知識分子的措施,如康熙皇帝或遣大臣或親往明皇陵祭拜,安撫漢人故國之心;尊孔讀經,重視漢族傳統文化,促進滿漢文化融合;恢復科舉考試,舉薦山林隠逸,籠絡漢族士人。通過如此一系列措施,有效拉近了漢族士人對滿族統治者的心理距離,减缓了其敵對情緒。特别是科考制度的恢復施行,使“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念自息”[13],自順治三年()至順治十八年()計舉行8次,録取進士人。[14]康熙朝續之,并多有加科,確實達到了牢籠志士、驅策英才的作用。這些都爲朱彝尊的政治轉向奠定了政策基礎。 與朱彝尊個人密切相關的是朝廷對於“通海案”人員的寬免政策。康熙二年()當局宣布“海贼入犯江南案内罪犯,奉有論旨除康熙元年()以前審結外,其餘亦從寬免”[15]爲朱氏的人生轉變提供了政治環境的可能性。 2.士人經世情懷的影響 名以文傳、學而優則仕是中國古代讀書人的一貫理想。作爲傳統文士,對不朽與濟世的渴望和追求是根植於血液的,朱彝尊亦是如此。參加抗清復明活動,除因家世原因對故明心存感懷與眷念外,無疑也是實現其政治理想的一個途徑。後復明無望,政治理想亦告破滅。在新政權逐漸穩固、社會漸趨安定、自身也重獲自由以後,經世濟民、名揚於世的情懷又重新復甦,而此時這一理想得以贲現的唯一途徑則是融入主流社會,出仕新朝。 朱彝尊起初認爲“游也,足以揚親之名”[16],以爲游幕即可播揚聲譽,同時通過協助幕主處理政務又能間接實現其濟世理想。故自順治十四年()先後客於楊雍建、曹溶、宋琬、王世顯、王顯祚、劉芳躅、襲隹育等人幕府中。游幕期間,通過近距離接觸清廷官員,對新近政治形勢的變化有了更充分的認識,這對朱氏放棄恢復故國的舊夢有直接的影響。但是,協助處理政務、參贊戎幕雖然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其經世之志,而“代人之悲喜,而强效其歌哭”[17]的實質處境,使他愈發感到“因人遠道非長策”[18]更激發了他走向前臺,實現政治理想的渴望。對功名渴慕等傳統文士情懷是朱彝尊政治轉變潜在的精神需求。 3.個人經濟狀况的促發 朱彝尊雖爲官宦之後,然家道中落,以至“行媒既通,力不能納幣”[19]衹得入贅歸安馮鎮鼎家。既建家庭之後,經濟狀况更是每况愈下,無家業、無俸禄,僅靠里中授徒、出外覓館維持生計,而束修之入常不足以供俯仰。加之幕主時有調動,朱彝尊文案之職也不能穩定保有,“妻兒空待米,風雨獨還家”[20]的狀况時有發生。順治九年()因無錢買藥長子德萬夭折,空餘“無錢輕藥物,瀕死念聰明”[21]的無限傷感。康熙二年()聞“通海案”得解,啓程歸里,途中仍在爲生計愁苦,感嘆“行李自憐垂橐返,田園生計轉茫然”[22]。 因爲貧困,家妻挨餓,大兒早夭,長期的困頓艱辛,使朱彝尊深感愧對妻子,順治十一年()有《贈内》詩,云“長貧真累汝,朝夕衹懷憂”[23],對家庭的愧疚使朱彝尊迫切希望改善自身處境,窘迫的經濟狀况是其政治轉向的直接現實因素。 内心文士情懷的涌動,蟄伏理想抱負的召唤,改善自身經濟狀况的迫切需要,加之現實政治、文化條件的具備,終於促使朱彝尊做出了政治選擇的重大轉變——融入新朝,尋求入世之路。 當然,朱彝尊由遗民自守向親附清廷的政治轉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這一轉變雖可以康熙十七年()應試博學鴻儒爲標志,但之前經歷了諸多内心的糾結挣扎與行動上的逐步過渡,由起初選擇仕隱之間的游幕謀生方式到最後應試博學鴻儒科出仕清廷,其中結附清廷要員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步。 [清]朱彝尊撰:《曝書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年(二)朱彝尊結附王士禛過程梳理 朱彝尊是一個有過抗清歷史的潦倒布衣,欲擴大影響,靠近新政權,結交文壇政界知名人士,是有較大難度的,他一直在思考尋找可依托之人而未遇,多有碰壁,嘗作“一刺懷中磨滅盡,回首風塵燕市”[24]感嘆貴人之難求。最終朱彝尊將王士禛作爲自己向正統文壇以至新朝接觸的良媒,通過投詩致信、直陳心迹、邀寫序文等方式主動結交王士禛,希望得到王氏的提携與幫助,提高擴大自身的名望與影響。 1.投詩致信,主動结交 康熙三年()閏六月下旬朱彝尊途經揚州,携詩主動拜會時任揚州推官的王士禛。然適逢王士禛至金陵公干,二人不及相見。王士禛於六月二十五曰收到朱彝尊的詩作與信函,展閲一過,大爲贊賞,作《答朱錫鬯過廣陵見懷之作時謁曹侍郎於雲中》一詩以爲回應。 遍檢朱氏詩文,未見所投詩信,此事賴王士禛《答朱錫鬯過廣陵見懷之作時謁曹侍郎於雲中》載之,後王士禛於《竹垞文類序》再提此事,云:“康熙甲辰,錫鬯過廣陵,投予歌詩。適予客金陵,不及相見。”[25]從王氏《答朱錫鬯過廣陵見懷之作時謁曹侍郎於雲中》詩中“破帽疲驢出雁門”及“曹公横槊懸相待,共醉飛狐雪夜尊”[26]等句可推知朱彝尊在書信中交待了自己四處游幕、疲於生計的落魄狀態。這次主動示好,一定程度上是緣於文人之間相互傾慕,以詩會友,但更深層的意義則是朱彝尊向文壇中心人物靠近的開始,這從朱氏康熙六年()所作的《王禮部詩序》可見其端緒。 2.直陳心迹,希望提携 康熙六年()王士禛邀朱彝尊爲其詩集作序,竹垞有《王禮部詩序》之作,於文中直接表達了希望得到王士禛提携的心聲。 《王禮部詩序》云: 彝尊幼而學詩,竊願望見作者之林。甲申以後,屏居田野,不求自見於當世。顧思得海内善詩之家,其辭之工可以出入風雅,必傳於後無疑者,而與之游,庶幾或附之以傳焉。蓋自十餘年來,南浮湞桂,東達汶濟,西北極於汾晋雲朔之間,其所交類皆幽憂失志之士。誦其歌詩,往往憤時嫉俗,多離騒變雅之體,則其辭雖工,世莫或傳焉。其達而仕者又多困於判牘,未暇就必傳之業。間或肆志風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爲標榜,不復商榷於布衣之賤。信夫,傳者之難,其人而欲附之以傳者又難也。……然則先生之詩其必傳於後無疑,而予之欲附以傳者,不可謂無其人矣。《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夫鳴鳥既遷於喬木,而必下呼其友。先生之交游滿天下,顧獨有取予之一言,是亦小雅之義也。[27]朱氏直陳自己渴望以才學見稱於世的心聲,以及可依附結交的贵人大家難得一遇的無奈,而王士禛則正是自己所求索的合適人選,明確表達了希望得到王士禛提携扶持的願望。 3.邀寫序文,借揚聲望 友朋推譽是宣揚名聲的重要有效途徑。順治十四年()朱彝尊於廣東結識屈大均,次年歸里,持屈大均詩作多方傳頌,屈氏之聲名因此遠播。屈大均於《屢得友朋書感賦》中有云:“得名自朱錫鬯始,未出嶺時,錫鬯已持予詩遍吴下矣。”[28]時朱彝尊之地位、聲望并不顯著,其贊譽宣揚尚能使屈大均嶺外聞名,若得有力之士若王士禛者爲之,效果可想而知。 “康熙中,其(王士禛〉聲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詩集,無不稱漁洋山人評點者,無不冠以漁洋山人序者。”[29]深諳此道的朱彝尊,抓住機會向王士禛邀序。康熙十六年()朱彝尊請王士禛爲自己的《竹垞文類》作序。[30] 康熙十七年()朱彝尊應試博學鴻儒科,而後出仕清廷,聲望漸起,逐漸著稱於正統文壇,仍兩乞序於王士禛:康熙二十七年()囑王士禛爲《日下舊聞》撰序[31],康熙四十一年()致信王士禛爲《經義考》邀序[32]。 張宗友著:《朱彝尊年譜》,鳳凰出版社,年三、王士禛提携朱彝尊考論康熙三年()六月,朱彝尊途經揚州,投詩拜會時任揚州推官的王士禛,主動結交王士禛,希望得到其提携幫助。而王士禛不負朱氏期望,在其出仕清廷之前,用多種方式對其提携幫助,對朱彝尊聲望與影響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王士禛提携朱彝尊過程考 王士禛對朱彝尊的主動結交給予了積極回應,在朱氏姓字達於禁中之前用多種方式對其提携: 1.作詩撰序揄揚朱彝尊才學 友朋的推譽是擴大詩文著述影響、提高文人學者聲望的重要途徑。以王士禛爲例,青年時期的王士禛即因得文壇領袖錢謙益的贈詩與撰序提升文壇地位。沈德潜《清詩别裁集》有云:“漁洋少歲即見重於牧齋尚書,後學殖日富,聲望日高,宇内尊爲詩壇圭臬。”[33]王氏亦自稱广虞山錢宗伯‘與君代興’之言暨贈詩‘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之句,實爲千古知己。”[34]而至康熙年間,王士禛已然大家,盛名滿天下,士人以得其一言爲榮,“得公一言,便自詡名士”[35],可見得王氏之推揚對於個人聲舂的巨大影響。 康熙三年()朱彝尊投詩拜會王士禛,王士禛得見詩作與信函後,賦有《答朱錫鬯過廣陵見懷之作時謁曹侍郎於雲中》,詩云:“桃葉渡頭秋雨繁,喜君書札到黄昏。銀濤白馬來胥口,破帽疲驢出雁門。江左清華惟汝在,文章流别幾人存?曹公横槊懸相待,共醉飛狐雪夜尊。”[36]對朱彝尊的來訪表達了欣喜之情,并對朱氏文學才華大爲贊赏,稱其爲江左第一。 康熙六年()秋朱彝尊自代州至京師,拜會時遷任禮部主事的王士禛,士滇賦有《朱錫鬯自代州至京奉柬》相贈,詩云:“短後曾將代馬騎,談兵絶塞偃牙旗。錦囊舊事悲唐壘,碧玉春流寫晋祠。燕世雪深衣褐敝,吴江楓落酒船遲。鴛湖若買三間屋,得便從君下釣絲。”[37]詩中表達了與之交好的意願,并再次對朱氏詩文高度贊賞。 康熙十六年()朱彝尊《竹垞文類》成,請王士禛賜序。王氏欣然允諾,爲作《竹垞文類序》。序中回顧了與朱彝尊十四載的交誼,對朱氏的文章學術作出極髙評價:“錫鬯之文,紆餘澄澹,蜕出風露,於辯證尤精。詩則舍筏登岸,務尋古人不傳之意於文句之外。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38] 以王士禛當時的身份地位,多次以詩歌、序文公開褒揚宣傳朱彝尊,雖不可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但對提高朱彝尊的名并與影饗之作用也是可想而知。 2.延請朱彝尊撰序作傳 康熙六年()王士禛詩集刊行,邀請朱彝尊撰序。竹垞受寵若驚,有《王禮部詩序》之作。 康熙十五年()王士禛妻張氏過世,請竹垞作傳,朱氏撰《張宜人傅》[39]。康熙十六年()王士禛囑竹垞爲其亡兄王士禛遺作撰序,朱氏撰《王考功遺集序》[40]。康熙十七年王士禛請竹垞爲其伯父王與胤撰碑文,朱氏撰《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41]。康熙二十七年()王士禛請竹垞爲其父王與敕撰碑文,朱氏撰《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新城王公墓碑》[42]。 朱彝尊爲王士禛詩文作序,與上文所論王士禛爲朱彝尊詩文作序,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康熙六年()之舉,當時王士禛已名滿天下,而朱彝尊還不過是一介布衣,上位者延請下位者爲自家詩文撰作序文,對於聲望的提高來説,受益的無疑是後者。 3.與朱彝尊同游集會 王士禛與朱彝尊定交之後多次宴集同游,兹舉幾例如下: 康熙十五年()王士禛、朱彝尊、田雯、曹貞吉、汪懋麟、林堯英、謝重輝、顔光敏等人泛舟通惠河,賦詩唱和。田雯《古歡堂集詩選》有《九月十日同北山阮亭兩先生實庵蛟門方山修來子昭良哉諸子介眉家兄泛通惠河屬鬱生作圖歌以纪之》一詩,後附朱彝尊、曹貞吉、林堯英、汪懋麟、顔光敏、謝重輝諸人和作[43]。 康熙二十三年()王士禛代祀南海,朱彝尊、魏坤、吴雯、查慎行爲之餞行,竹垞有《送少詹王先生士祺代祀南海兼懷梁孝廉佩蘭屈處士大均陳處士恭尹》,其他三人亦各有詩[44]。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王士禛、朱載震、朱是名、查嗣璨、趙執信、王戟於竹垞家宴飲,共賞朱氏所藏米海嶽研山。王氏先後有《米海嶽研山歌爲朱竹垞翰林賦》《再題研山絶句示竹垞》以記之[45]。 康熙二十八年(〉社日王士禛、朱彝尊、徐乾學、陳廷敬登黑窑廠,聯句賦《社日登黑窑廠聯句》[46]。 康熙二十九年()王士禛、朱彝尊、王澤宏、査慎行、陳奕禧、孫致彌共游京城西郊,聯句賦詩《燕京郊西雜咏同諸君分韵》[47]。 集會宴游、唱和酬贈看似文人墨客問的風流雅韵,實則具有溝通感情、擴大交際範圍的實際作用。王士禛與朱彝尊多次同友人共游,無疑是彼此融入對方社交圈的絶好機會。而就朱王二人相較,王士禛成名在前,二人的交游,特别是交游的前期,王士禛不論在主流文壇還是在官僚政界的影響都高於朱彝尊,其所結交,多官員與名士。故這種社會圈子的相互引薦與融入,就聲望的提升與影響的擴大來説,獲益多者無疑是朱彝尊。 [清]李斗著;王軍評注:《揚州畫舫錄》,中華書局,年(二)王士禛提携朱彝尊之原因 與王士禛交游之初,朱彝尊是一個有着抗清經歷的潦倒布衣,這一敏感的身份對於朱氏結附貴人是一個很大的不利因素。順治十七年()朱彝尊嘗憑曹溶之薦謀事於宋琬,而最終不了了之,其主要原因即是朱氏的抗清經歷。而處於仕途上升期的王士禛却敢於并樂於接納朱彝尊,并在多方面予以幫助提携,建立了深厚的交誼。其中原因,關涉王士禛與朱彝尊兩個方面: 1.王士禛性好交游,樂於提携微末 王士禛性喜交游,未出仕前即常與文士集會唱和,最爲著名的即是順治十四年()八月集邱石常、柳藉、楊通久、楊通睿等一時才彦於大明湖集會賦詩。而後順治十五年()五月與張一鵠、汪琬、許珌、王翰臣等宴集酬唱;同年夏秋,與汪琬、程可則、鄒祗謨、許珌、李念慈、張一鵠等又有多次集會唱和。 順治十六年()王士禛抵京,常與汪碗、程周量、劉體仁、粱熙、葉方靄、彭孫遹、陳廷敬等往還唱和;同年中秋與吴綺、韓詩、陳祚明、周容等集梁園分韵賦詩;重陽節與曹爾堪、彭孫遹等於黑窑廠登高賦詩;同年又與李敬、董文驥唱和。故汪琬嘗云:“新城王子居京師,與其友唱和爲詩甚樂也。”[48] 順治十七年()王士禛任揚州推官,與文士集會唱和愈加頻繁。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四年()王氏於揚州期間,與之同游集會唱和者有確切文獻可考的即有36人,故其兄王士禛稱其“爲揚州法曹,日集諸名士於蜀岡、虹橋間,擊缽賦詩”[49]吴偉業亦稱“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50]。 王士禛交游廣泛,并樂於提携輕微,故頗多布衣之交,其於《漁洋詩話》自稱:“余在廣陵五年,多布衣交。”[51]順治十八年()作《歲暮懷人絶句》六十首,云“詩中所及,大半布衣也”[52]。對於富有才學的貧寒之士王士禛尤能折節下士,提携扶持。如康熙二年()王士禛偶讀貧苦布衣吴嘉紀《陋軒詩》,遂主動飛書致意,爲其撰寫序文;康熙三年()修禊紅橋,王氏又邀吴嘉紀與諸名士唱和。原本“天下之人不知之,鄉曲之人不知之,即其妻孥亦且駭异唾棄之”[53]的吴嘉紀,經由王士禛的引薦逐漸步入名士之列。又康熙四年()春王士禛親訪通州布衣邵潜,“下車徒步行入”[54],“引滿數觴,盡歡而罷”[55]同年三月初三日又邀邵潜同與冒襄水繪園集會。 康熙四年()下半年王士禛至京師爲官,名望愈隆,仍熱衷於扶持後進,“在京師,務汲引後進”[56],故而四方士人多携詩拜謁,“多樂就之”[57]。 王士禛樂於提携後進,因之受益者頗多,“四方之士以齒頰成其名者甚衆”[58]。而同時王氏也因此友朋門生遍布,誠如袁世碩所言“後進之士多入其門,私淑執弟子禮者幾遍天下”[59],獲得了衆多的支持與擁護,這也形成了他日後成爲一代詩壇盟主的重要基礎,如蔣寅所言“要成爲詩埴盟主,他也需要積累許多提携、品題寒素和後進的業績,以贏得同儕和後輩詩人的擁戴”[60]。 2.王士禛同情抗清活動,多與明遺民相善 考察王士禛的交游情况,會發現其與衆多明遺民過從甚密,其中不乏參加反清復明的激進遗民。現據蔣寅《王漁洋事迹徵略》,以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四年()王士禛於揚州推官任内爲限,對王士禛與明遺民的交往活動 梳理如下(上標數字指該書頁碼): 時間 同遺民之交往 順治十八年()三月底 結交遗老林古度68 順治十八年()三月底 結識“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襄68-69 順治十八年()三四月間 親訪“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襄69 順治十八年()冬 冒襄過訪80 康熙元年()五月 林古度、冒襄、杜浚、唐允甲等遺民爲其《漁洋山人詩集》作序86 康熙元年()六月十五日 與袁于令、杜浚、邱象随、蔣階、朱克生、張養重、劉梁嵩、陳允衡、陳維崧等大量遺民紅橋集會,結有《紅橋倡和集》88 康熙元年()七月初七 方文過訪90 康熙二年()九月 與方文同集廣陵貴家,對其遗民氣節大爲稱道 康熙二年()重陽節 與遺民方文、黄傳祖游觀音閣 康熙三年()正月初七 雪中訪杜浚 康熙三年()三月初九 與林古度、程邃、孫默、孫枝蔚、杜浚等遺民修禊紅橋 康熙三年()春 送孫默歸黄山 康熙三年()十二月 與孫枝蔚酋信往還 康熙三年()除夕 爲林古度删訂詩集 康熙四年()二月底 訪冒襄 康熙四年()上巳 與邵潜等至冒襄水繪園集會 康熙四年()春 與程康莊議刻林古度詩集 康熙四年()五月 與林古度晤於金陵 康熙四年()五月 訪方文 康熙四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 與方文訪名山古刹- 康熙四年()五月 寄金陵所作詩與孫枝蔚 康熙四年()七月初七 方文、孫枝蔚等爲其送行 王士禛不僅與衆多前朝遺民維持着良好的關係,對激烈抗清的貞烈之士也嘗以文字進行頌揚。“揚州十日”期間,揚州知府任民育全力抗争,以身殉節。王士禛爲其作傳云:“天兵至,論降,民育不可,飲刃死。揚人聞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隕於署,櫪馬皆驚。”[61]對一抗清殉明的官員作如此正面的描述,充分反映出王士禛對抗清人士的態度與感情。 蔣寅:《王漁洋事跡徵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此外,王士禛還嘗於危難之際,以身犯險,周全保護了大量參與“通海案”的遗民。順治十八年()清廷徹查“通海案”,督辦在側,大量官員因査辦“通海案”餘黨不利而下獄。在這種情形下,王士禛“理其無明驗者出之,而坐告訐者”[62]曲意回護了一大批曾響應鄭張抗清的官民,“全活無算”[63]。 在新朝初建的非常時期,作爲清廷官員的王士禛與明遗民交往密切,并且對抗清人士心懷同情,無疑是很大贍而且微妙的。嚴迪昌認爲“漁洋山人的詩學學術交游或唱和酬應活動實在是多與權術心機相輔而行的”[64];亦有論者將王士禛與明遺民的主動交好解讀爲一種刻意的策略和姿態,用以打開江浙地區遺民盤踞僵硬的政治局面;或認爲王士禛揚州五載與明遺民過從是爲贏得清初影饗巨大的遺民群體的支持,從而爲執文壇牛耳奠定基礎。我們并不否認會有這些因素的存在,但如果考察王氏的家世淵源及其家族所經歷的變故,或許能得到更爲直接與符合情理的解釋。 新城王氏爲明末山左望族,王士禛高祖王重光於嘉靖朝官至貴州按察使參議;曾祖王之垣於萬曆朝累官至户部左侍郎;伯祖王象乾萬曆間官至兵部尚書;嫡祖王象晋於崇禎朝官至浙江右布政使;其他袓、父輩在明朝以科第入仕者,還有王象坤、王象春、王象復、王與胤等多人[65]。崇禎十五年()冬清兵屠城濟南,兵臨新城,王氏族人和當地民衆頑强抵抗,在這場劫難中有相當數量的王氏族人遇難,其中包括王士禛伯父王與朋,叔父王與玫,從兄王士熊、王士雅、王士和等十一人[66],從伯母、從嫂等五位女性族人亦殉節[67]。崇禎十七年()甲申之變,王士禛伯父監察御史王與胤與妻兒皆自缢殉節[68]。祖父以浙江右布政使歸里不出,自號明農隱士,名入《皇明遺民録》[69]。父親則以家父年邁、兄長殉國爲由拒絶有司舉薦,不仕新朝。 王士禛幼年經歷易代浩劫,家族多人被殺、殉節以及祖父輩的守節不仕對王士禛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嘗云“予兄弟少無宦情,同抱箕潁之志,居常相語,以十年畢婚宦,則耦耕醴泉山中,踐青山黄發之約”[70]。可見其少年時并無仕進之心,即便順治十二年()會試中式,“未殿試而歸”[71]可見其當時的矛盾心理。後雖因保全、振興家族等多種原因而參加科考,出仕清廷,但家族所經歷的巨變肯定對其有着深刻影響,如高橋和巳所言:“少年時代經歷的造次顛沛——漢族政權明王朝的滅亡,仍然長期地成爲他悲哀的根源。”[72]隨着形勢的發展與身份的轉變,王士禛與明遗民的關係縱然摻雜了若干功利目的,但其思想深處的心結應該仍然是其與明遗民交善的主要根源,如蔣寅所云,王漁洋能赢得整個江南遗民詩群的真誠賞愛,其言語文辭、性情舉止,必定有足够的真誡。”[73] 3.朱彝尊博洽多聞,詩文俱佳 王士禛願意結交并提携朱彝尊,除了朱氏身份經歷符合王士禛同情抗清人士、樂於提携後進的一貫作風外,朱彝尊自身深厚的文學與學術修養是二人能够定交并得以持續交往的更爲重要的因素。 朱彝尊博聞强識,出經入史,在多個領域的成就都可入清初一流大家之列。皇子胤扔曾稱之爲“海内第一讀書人”[74]。《清史稿·朱彝尊傳》有云,當時王士禛工詩,汪琬工文,毛奇齡工考據,獨彝尊兼有衆長。”[75]雖然以上是對其生平最高成就的評價,但於康熙初年朱彝尊多方面的才能已經嶄露頭角。 早在順治十五年()王士禛初見錫鬯嶺外詩,即“嗟异之”[76],之後康熙三年()與康熙六年()朱彝尊兩次拜會王士禛,王都有詩記之,在此二詩以及康熙十六年()爲朱氏《竹垞文類》所作的序中對朱彝尊之詩文學術给予了高度評價。王氏的這種評價不能簡單地歸入文人間的相互標榜,王士禛不僅對於自己的詩歌創作要求甚高,素有“愛好”之稱,對他人的詩文也不會輕易施以溢美之詞,惠棟嘗稱王氏“於朋輩詩文就質,凡有得失,亦必直言無隱。宣城施愚山常曰:‘吾交游滿天下,直諒多聞,惟王先生耳’”[77]。甚至於“有京朝官以詩相質,山人爲指摘篡改,不少隱,其人頗有愠色”[78]。王士禛如此多次毫不掩飾地稱許朱彝尊的文采學問,可見他是由衷的認可與贊賞。 并且在與朱彝尊的交游過程中,王士禛於學術上獲益頗多,得以開闊視野、增長見聞,甚至得到學術指導,這也是二人能够持續深入交往的重要基礎。而隨着朱彝尊名位日顯,聲望愈隆,其在文壇學界的地位影嚮漸與王士禛相埒,朱王之間結附與提携的關係亦逐漸淡化,各方面的相互交流、各取所需遂成爲二人交游的主要内容。 嚴迪昌:《清詩史》,浙江古籍出版社,年四、結語朱彝尊與王士禛同爲清康熙一朝文壇名宿,以“南朱北王”并稱,然兩人并非同時顯名於正統文壇,存在着先顯與後起、結附與提携的關係。王士禛進士出身,仕途平順,青年之際即名顯文壇;朱彝尊則初期以遗民自守,後在多種因素的促使下决意融入主流階層,親附新朝。朱彝尊以王士禛爲結附對象,希望通過王氏的提携引薦來完成自己走上主流文壇、融入新朝的人生轉折。王士禛則基於對朱彝尊遗民身份的同情、卓越才學的欣賞等因素,欣然與之定交,以詩文贊譽、同游集會等多種方式給予朱彝尊提携與幫助,對朱彝尊聲望與影響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隨着朱彝尊名位聲望的日益顯著,朱王二人之間結附與提携的關係逐漸淡化,相互幫助、各取所需成爲二人後期交游的主要特點。而朱王二人的結交也反映了清初歷史背景下社會、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豐富内容,是清初文人交游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典型案例。 (向上滑动启阅) 参考文献[1][清]趙執信著,趙蔚芝、劉聿鑫注釋《談龍録注釋》,齊魯書社,年.第75頁。 [2][清]鄭方坤《曝書亭詩抄小傳》,載其《國朝名家詩抄小傅》卷一,光緒十二年()萬山草堂刻本。 [3][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載其《王士禛全集》,齊魯書社,年,第頁。按:孫星衍《刑部尚書王公傳》云王氏“順治十二年成進士”(見[清]錢儀吉《碑傳集》卷十八,中華書局,年,第頁),沈德潜《清詩别裁集》卷四云王氏“順治乙未進士”(見[清]沈德潜《清詩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六云王氏“順治十二年成進士”(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六,中華書局,年,第頁),皆誤。 [4][清]王士禛《菜根堂詩集序》,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5][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箋校《錢牧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6册,第頁。 [6][清]趙翼著,馬亞中、楊年豐批注《甌北詩話》,風凰出版社,年,第頁。 [7][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嶽麓書社,年,第百, [8][清]沈岸登《黑蝶齋小牘》,載[清]徐釚《本事詩》卷十一,乾隆二十三年()桐鄉汪肯堂半松書屋刻本。 [9][清]朱彝尊《王禮部詩序》,載其《曝書亭集》卷三十七,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 [10]鄧之誠《淸詩紀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 [11][清]王士禛《朱垞文類序》,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12][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册,台灣商務印書館,年,第頁。 [13][清]巴泰、圖海、索額圖等修《世祖章皇帝實録》卷十九,《清實錄》第3册,中華書局,年,第頁。 [14]參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三聯古店,年,第—頁。楊淑艷《論康熙帝對漢族士大夫的懐柔政策》(見《黑龍江社會科學》年6期,第64頁)據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録》統計,作“人”,誤。 [15][清]馬齊、張廷玉、朱軾等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卷八,《清實録》第4册.第頁。 [16][清]朱彝尊《孫逸人壽序》,載《曝書亭集》卷四十一。 [17][清]朱彝尊《報周青士書》,載《曝書亭集》卷三十一。 [18][清]朱彝尊《寄表弟查容》,載《曝書亭集》卷四。 [19][清]朱彝尊《亡妻馮孺人行述》,載《曝書亭集》卷八十。 [20][清]朱彝尊《歸》,載《曝書亭集》卷三。 [21][清]朱彝尊《哭萬兒》,載《曝書亭集》卷二。 [22][清]朱彝尊《歸次皋亨山作》,載《曝書亭集》卷六。 [23][清]朱彝尊《贈内》,載[清]馮登府、朱墨林輯《曝書亭集外稿》卷二,清嘉慶二十二年()刻道光二年()阮元印本。 [24][清]朱彝尊《百字令·自題畫像》,載《曝書亭集》卷二十五。 [25][清]王士禛《竹垞文類序》,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26][清]王士禛《答朱錫鬯過席陵兄懷之作謁齊侍郎於雲中》,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27][清]朱彝尊《王禮部詩序》,載《曝書亭集》卷三十七。 [28][清]屈大均著,歐初、王貴忱主编《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年,第頁。 [29][清]永瑢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冊,第頁。 [30]張宗友《朱彝尊年譜》,鳳凰出版社,年,第頁。 [31]張宗友《朱彝尊年譜》,第頁。 [32]張宗友《朱彝尊年譜》,第頁。 [33][清]沈德潜《清詩别裁集》,第頁。 [34][清]王士禛《與林佶》十二,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35][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惠棟注,載《王士滇全集》,第頁。 [36][清]王士禛《答朱錫鬯過廣陵見懷之作時謁侍郎於雲中》,載《王士禛全集》,第百。 [37][清]王士禛《朱錫鬯自代州至京奉柬》,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38][清]王士禛《竹垞文類序》,《王士禛全集》,第頁。 [39]張宗友《朱彝尊年譜》,第頁。 [40]張宗友《朱彝尊年譜》,第頁。 [41][清]朱彝尊《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載《曝書亭集》卷七十二。 [42]張宗友《朱彝尊年譜》,第頁。 [43]張宗友《朱彝尊年譜》,第頁。 [44]張宗友《朱彝尊年譜》,第頁。 [45]張宗友《朱彝尊年譜》,第頁。 [46]張宗友《朱彝尊年譜》,第頁。 [47][清]朱彝尊《燕京郊西雜咏同諸君分韵》,載《曝書亭集》卷十五。 [48][清]汪琬著,李聖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人民文學出版社,年,第頁。 [49][清]李斗著,王軍評注《揚州畫舫録》,中華書局,年,第頁。 [50][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51][清]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中,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52][清]王士禛《居易録》卷四,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53][清]王士禛《悔齋詩集序》,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54][清]王士禛《居易錄》卷四,《王士禛全集》,第頁。 [55]蔣寅《王漁洋事迹徵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第。 [56][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57][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58][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惠棟注,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59]袁世碩《王士禛全集前言》,載《王士禛全集》,第1頁。 [60]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鳳凰出版社,年,第頁。 [61][清]王士禛《任民育楊定國傳》,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62][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惠棟注,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63][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惠棟注,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64]嚴迪昌《清詩史》,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第頁。 [65][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王士禛全集》,第-頁。 [66][清]朱溶《王與胤傳》,載其《忠義傳》卷二,[明]姜垓、[清]朱溶等撰,高洪鈞等整理校點《明清遺書五種》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年,第-頁。 [67]参[清]王士禛《五節烈家傳》,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68][清]朱彝尊《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載《曝書亭集》卷七十二。 [69][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惠棟注,載《王士禛全集》第页。 [70][清]王士禛《癸卯詩集序》,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71][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載《王士禛全集》,第页。 [72]朱則杰《朱彝尊研究》附錄,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第頁。 [73]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诗壇》,第。 [74][清]朱桂孫、朱稻孫《皇清欽授徵仕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顯祖考竹垞府君行述》,載[清]朱彝尊著,王利民等编《曝書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第。 [75]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第頁。 [76][清]王士禛《竹垞文類序》,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77][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惠棟注,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78][清]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惠棟注,載《王士禛全集》,第頁。 本文原載《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三輯上卷,p-。圖片來自網絡,引用請據原刊。(长按图片或扫描图片识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erfenga.com/nefyfyl/8319.html
- 上一篇文章: 古诗词中的春春花春柳
- 下一篇文章: 强直性脊柱炎夏日抗病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