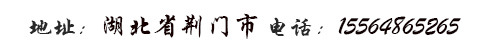周肇祥及其游龙洞
|
藏园老人傅增湘游览龙洞,不是一个人去的,在陪同他的友人中,有一位叫周肇祥。 周肇祥(-),浙江绍兴人,号养庵,别号退翁,无畏居士,清末举人,曾就学于京师大学堂。在晚清和民国,任四川补用道、奉天劝业道、署理盐运使、临时参政院参政、葫芦岛商埠督办以及湖南省长、临时参政院参政、清史馆提调、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等,多年主持中国画学研究会,是画坛的领袖人物。 他码字的水平极高,写的文章很耐读,既涉笔成趣,又意蕴深厚,如醇厚的美酒,如浓郁的佳肴,那些字不装、不夸,不吹大话,字字流露真性情,读来恍如隔世。作家董桥说:真好看,文字上流,文得清丽,现代人写不出了。周肇祥曾著有一本《琉璃厂杂记》,董桥说:“那本书我翻烂了。” 周肇祥文质彬彬,满腹经纶,蓄有美须髯,人称“周大胡子”或“周胡子”。虽然他是画坛的代表性人物,但更看重读书人和官员的身份,对人以“中华美术家”称呼他,他曾颇生感慨:“嗟乎,周生读书万卷,从政廿年,而竟以美术家名耶,可悲也,亦可幸也。” 周肇祥是有故事的人,早年风光无两,晚年落寞凄惨。上半生,他快意官场,收藏金石古玩,寄情山水之间,在北京西山筑退谷别业鹿岩精舍,建水流云在之居,诗酒风流,长期执掌北方画坛之牛耳。关于调任北京以前的日子,他在《琉璃厂杂记》之中说:“住京凡十日,谒总统,访师友,酬应征逐,殊鲜暇晷。先后游海王村凡六次,行箧少余钱,商订少良好,所得只此。然吾辈敢足自娱而已,非与有力而好事者争多靡斗也。” 关于他晚年的资料,则很简略,比如:“年,庚寅,70岁,被捕入狱;年,甲午,74岁,去世。”周肇祥外号无畏居士,面临巨变,能无畏乎? 他的一生,先繁华而后冷落,古稀之年,被抄家、批斗、入狱,曾经的精舍已是陋室空房、家徒四壁了。美髯不再,神情颓丧,面目全非,仅靠糊纸盒聊以糊口。昔日欢笑,那可复得?“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时移事变,生死易途,所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也。” 游览龙洞的时代,虽然战乱不已,但周肇祥的生活还很滋润宽裕。从龙洞庄到龙洞寺,车不通行,他雇了个轿子,说“赁资才一金”,那个时候,一金能买多少东西啊。这次随同傅增湘游历山东,周肇祥是有备而来的,他带着拓字的全套家伙,见到入眼的石刻,就拓下来。当然,他博通文史,精于金石,眼光很高,能看上的石刻不多,但是在龙洞佛峪却收获多多。他虽然对明朝碑刻不屑一顾,但是对龙洞的明朝雪蓑子的碑刻大感特异,当然就拓了下来。 此前发了篇文,介绍傅增湘及其游龙洞,太极云兄留言说,傅增湘在文中怎么没有提及萧培元的诗。我猜测是他的眼界高,看不上近人的诗作。看来,周肇祥也有这个偏好,泥古不化,都是老学究,是老派文人。 周肇祥满肚子学问,每看到石刻,都知道后面的故事,比如龙洞有宋崇宁二年张颉、李倚、范庭坚、刘琮、李佳联辔来游题名,他就写道:“张颉,金陵人,以直集贤院知齐、沧二州,才而无德,苏辙尝论其九罪。拱辰,铎幕僚;而李倚辈,颉之丞尉也。” 胸有诗书,周肇祥颇自负,眼界颇高,看不上的东西,往往直言不讳,也是有趣之人。比如,对于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上的展品,他说,“惜前日选印时,一任诸少年为之,未能慎择,颇多幼稚之作”。 对于诸少年关于日本家藏书画的赏鉴,他说,“用笔设色,种种器物皆与宋法合。而孺子辈从旁乃云绢无光,疑非宋,宋绢密緻,久而黯淡,未闻以有光为鉴定之据,可谓妄语矣。” 在前半生,周肇祥不差钱,但也没有到挥金如土的份上。据史树青,周肇祥即便雅好收藏,也只是到冷摊小市上去慢慢淘,琉璃厂那样的地方也去,贵的买不起,回来记上一笔,就成为很耐读的小品文;抑或淘到便宜的金石书画,往往也写上一笔,普通的物件,哪怕是锱铢小器,平常的书画碑帖,一经他的品题,便顿生异彩。 比如,他有一方砚,上面刻铭曰:“鼍几石,坚老胜。譬诸直谅苦且硬。好置座隅药我病。乙丑正月,肇祥。”他自己刻有一个收藏印,文曰:“周肇祥小市得”。寄托辛苦搜求,得来不易也。 由俭入奢易,奢入俭难。从穷困到繁华,烈火烹油,锦上添花,固然可以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从繁华到冷落,笏满床变成了陋室空堂,歌舞场变成了衰草枯杨,更让人唏嘘不已。有此经历的,其中冷暖,外人不可道也,自知也。周肇祥与曹雪芹,有着相似的晚年经历。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曹雪芹经历过家事大变,他晚年著书黄叶村的故居,离周肇祥的退谷不远,退谷中有许多景点还与红楼梦有关,如“木石前盟”等。 周肇祥对龙洞和佛峪的记述,信笔写来,字字珠玑,从容不迫,评鉴历史,关怀文化,尤其让我欣赏的,是他从龙洞到佛峪途中的偶遇,“途遇士女行歌,目送老人,谓可入画。不知彼身亦在画中,相与一笑。”这是一副多么迷人的画啊。一个旧时夫子,一个糟老头子,心里也有强烈的爱美之心。 比起码字,周肇祥更精于画笔,这位搅动他心扉的女孩子,一定会出现在他的画中,因为,他的画笔如何会辜负那久久不愿舍离的倩影。如此,那一幕才能在周肇祥不老的心中成为永恒。置身画室,相与一笑,这老夫子不知有着怎样的幸福,他一定希望再来龙洞的。也许,读过他龙洞游记的友人会与他开玩笑,说他动了心,说他发了情,那么,他是否会也像孔夫子那样,脸红脖子粗地急急辩解,“天厌之!天厌之!” 如今,那个画中的士女不知走到了哪里。周肇祥肯定走入历史了,他的退谷别业里的古造像、金代经幢、碑石等,早已化为云烟。只是,他在龙洞和佛峪拓下来的雪蓑子的碑刻以及金《亨法师塔记》、元《重修灵惠公祠记》、唐《遇缘造阿弥陀佛记》等,现在的命运如何? 户外徒步,有时独行,更多的是同行。户外归来,我会码几个字,同行的有雅兴的驴友往往也会或美篇,或博文,记录驴行中的山川秀美和欢歌笑语。同样的驴途,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感受,但有着同样的开心愉悦。有一次,我码了些字,大师有大作,美林有佳文,爱家有日记,除了我乱扯,那是精彩纷呈,同行的驴友都击节叫好,有的还不嫌事大地起哄,要来个大比拼。 周肇祥和傅增湘的龙洞游记,也是如此。俩人都是弄文字的高手,而且有古今兼通的学问,尤其是,他俩做事还都认真,来山东旅个游,不仅之前穷经问典,还携带着山东好几个地方的县志和相关的文献。两位大家的龙洞游记,由于各自的性格、喜好和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erfenga.com/nefrybw/8315.html
- 上一篇文章: 天水文学王钰电视短剧牛牛和巧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