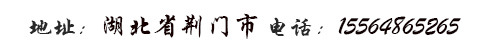奇石讲堂观赏石文化二
|
源远流长的申国观赏石文化 1、新石器时代―观赏石文化的萌芽时期 观赏石文化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两三百万年前,人类的始祖猿人把石头敲砸成为一件件粗糙的武器和生活用具,在山燧取火时,就拉开了石器时代和吃熟食的序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出现了供玩赏和化妆(染色)的石头。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过赤铁矿碎块(粉末)和许多玩赏矿物(玛瑙、叶蜡石、滑石、绿松石、碧玉、软玉、硬玉与蛋白石等)。山顶洞人生活在大约1.3万——2万年前,原来,在那茹毛饮血的年代,人们依然爱美,依然需要精神文化生活。说近点,大约五六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层中发现陪葬用的小石子,也足以说明那时候人们早就开始与我们一样欣赏石头了。 从那时候起,人类社会始终与石头结伴而行。劳动创造了人,并进入了观赏石文化的萌芽时期。 无论是北方的山顶洞人还是南方的河姗渡文化,也无论是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或者新疆广裹无垠的土地上,从几十万年前直延续到五六千年前的文化层中,都发现了古人赏石的遗迹。譬如距今约2.8万年前峙峪人制作的石墨装饰晶、安阳小南海的带孔石珠、人汶口化和年前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中的原石殉葬品、装饰品和雨花石,都表明赏石已成为人类审美活动中的重要对象之一。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在——年前,即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玉器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古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一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伟大的思想家。姑且不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得对观赏石文化的影响;单说与之同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和老子的哲学思想给此后的观赏石文化无疑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赏石和美学观点。孔子的君子以玉比德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观点,老子的自然、返璞归真之说和道法自然的理念,以及此后承学老子之术的庄子,论主客两忘而物化的审美观,都影响着后世的赏石理念和艺术创作。这些赏石和美学思想深深地烙印在《山海经》和《尚书》的“禹贡”之中。《山海经》中曾提到各地名山产出的观赏石;珉、美石、婴石、彩石、文石、硌石、怪石和磐石等。据考证,它们之中有的属于玉石有的是指图纹石或造型石。“禹贡”中有地方官员上贡皇室的青州铅松怪石和由灵壁石制作而成的磐——徐州泗滨浮磐。 秦代建造阿房宫,宫中筑园林、造假山,开园林缩景艺术和园中欣赏石头之先河。汉代对后代观赏石文化的影响,在于当时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连带将佛教与观赏石文化的渊源一起给中国吹进了赏石之风。后人以为随后干余年曾在中国盛行的“禅石”就起源于佛教。禅石讲求“五德”无相、自然、寂静、沉稳和圆润,讲求稳重古朴,怡淡优雅、肃穆幽玄,强调赏石要使人神思安定,心绪清淡,心灵沉稳,这些部是佛教教义的理念在赏石活功中的深刻反映。 2、魏晋南北朝―观赏石文化的兴起时期 在民间赏石的基础上,到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当时政局动荡,吏治黑暗,文人学士不满现实而又十力抗争,于是纷纷隐居山林,寄晴于山水之间。不想,这种逃避现实的做法竟陶冶出不少田园诗人,如谢灵运创作的田园诗、山水诗名噪一时东晋诗人陶渊明更是将旖旎的田园风光与奇石超凡脱俗、孤傲贞洁禀性融人作品,他崇尚自然,博学善文,尤喜雅石。他的九江寓所后院有块“醉石”,在他朦胧醉卧之时便下榻其上,他也由此而被后人尊为赏石鼻祖。清代诗人袁枚诗曰:“先生容易醉,偶尔石上眠。谁知一拳石,艳传千百年。金床玉几世恒有,眠者一过人知否?不如此石占桑,胜立穹碑万丈长。” 从魏晋到南北朝,听观赏的石头多是苑囿庭园中的园林石,中型和小型的园林石被蒐集于自家的庭园之中。梁代建康同泰寺(今南以鸡鸣寺)前有皇上赐封的四块奇丑无比的“三品石”和梁武帝与大臣到溉下棋赢取的“奇礓石”(又名“到公石”),都是那时候的遗迹。千年后此石辗转落人袁枚之手,他又作诗曰:“到公有奇石,曾向华林补。千年幽人得,风月一齐古。当作石交看,摩挲日三五。” 3、唐宋―观赏石文化的繁荣时期 唐宋时期赏石、藏石、玩石风兴盛,不愧是中国观赏石文化的繁荣时期。赏石大量进人宫廷花园和白宦人家,诗人、文人骚客对赏石情有独钟,大大提高了赏石的文化品位。唐宋文人雅士,社会名流收藏奇石自不待说,拜石者有之,为石吟诗作赋者有之,为石树碑立传者有之,甚至有为一块雅石争斗引发龃龉,被后世传为笑淡。 唐代宰相李元卿是一位赏石家,藏有“罗浮山”和“海门山石”等名石;位列宰相、大子之师的牛僧儒,也以偏爱太湖石著称、对赏石遁入了“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的若痴如醉境界。同时代的李德裕、皮日休和白居易等人,也都是类似的“石痴”。白居易酷爱大湖石、为之作有名篇“太湖石记”,从形、质、姿、势、怪、丑、老、灵、气、色和纹诸方面赞赏太湖石之美;苏东坡补充了大湖石的“清”、“丑”、“顽”和“拙”之美,提出“石文而丑”的理论。 浙江绍兴有一“炉柱晴烟”的名胜旅游点,就是隋唐时期采石的遗迹,后人奉若神明,也是宋人米芾“抱石而眠”之地。 到了宋代,赏石之风更盛。诗人、词家、书法家、画家统统爱上了奇峰雅石。苏东坡、米芾、叶梦得、黄庭坚、陆游、欧阳修、范成大、文同、杜绾、梅尧巨和苏舜钦,既是文墨大家,也都是爱石成癖者;他们为石吟诗作画,为石“树碑立传”,甚至与石“称兄道弟”。 号称“石癫”、“石痴”的米芾,曾经提出过品赏雅石的“秀”、“痠”、“皱”和“透”四字诀(后被清代画家郑板桥指为“瘦”、“漏”、“透”、“皱”),被后人奉为圭臬。米芾或见奇石便拜,或抱石而眠;苏轼为奇石作“枯木怪石图”、写诗作赋传为佳话。他在《壶中九华》中写直“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五岭莫愁千嶂外,为华今在一壶中。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明处处通。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有趣的是,这个“石迷”太守,在从杭州告老还乡时,谢绝了一切礼品和宴请,却唯独“笑纳”灵隐寺惠净禅师的一块天竺石,说:“白居易是‘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现在的天竺石更珍贵了。我不知去了多少回,一件也没有弄到,今天得到了,总算如愿以偿了”并赠诗言谢:“在郡依前六白日,山中不记几回来。还将天竺一峰去,欲把云根到处栽”。 沈括是北宋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既熟读天文、地理、地质和医药,又精通文学、历史、音乐和美术,还是一个遇奇石便口称“兄弟”的赏石迷。 北宋第八代皇帝宋徽宗,搜集闻名的“宣和六十五石”。阿谀奉承者投其所好,以“花石纲”搜刮民财,大肆收罗民间的奇花异草和雅石怪岩,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宋代有很多文豪为雅石“树碑立传”:藏石家孔传撰有专著《论石》,欧阳修特别钟情菱溪石,为之著《菱溪石记》。杜绾于年编著了最早的赏石系统性文献《云林石谱》,除了录入传统的观赏石外,还记载了矿物晶体和化石,为后世听沿袭引用,成为“石谱”的开山鼻祖。随后又有范成大的《太湖石志》、渔阳公的《渔阳公石谱》和赵希鹊的《洞天清禄集》等数部专著问世。这些专著的功绩是把奇石的地位提升了一个层次——将赏石与古琴、古砚一起划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瑰宝的文房四宝之列,也在乱世之中为后人留下厂不可多得的文字资料。 从现存的资料看,元代赏石不很兴盛,只有少数上层人士(如官吏、画家)和佛道参与收藏、赏石和石谱编著。 4、明清―观赏石文化的鼎盛时期 明清两代的赏石文化达到鼎盛时明。表现在赏石文化全面向文人雅士的庭园、书斋享阁和文化领城渗透,与丝竹之声相配,融入文章、书法、美学和绘画,成为“雅”与“俗”的分野。 明清两代爱石、藏石、玩石的文人雅士“队伍”中增加了学者的色彩,他们成了研石队伍中的带头人,最典型的为徐霞客。作为地理学家的他考察了北起津、冀、南抵粤、柱、黔、滇的广大地区,研究了喀斯特地貌的分布和成因。这支队伍中还有《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画家郑板桥和林有麟等。很多人知道郑板桥是为画家,尤擅长画竹,殊不知他也皓爱奇石,研究奇石,他提出了奇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的理论,从“丑石”身上竟还能休味出“雄”和“秀”来,难怪他画起画来得心应手而独有创造,写起字来龙飞凤舞而独具一格。他说自己“难得糊涂”,其实他是最“清醒”的,造“众人皆醉我独醒”。据说.他在挚友毕际友家坐馆三十余年,从毕家的奇石中选出十块佳石,称为“十友”,日日赏石作诗,夜夜勤于写作,终成“大家”。最难得的是万历年间的林有麟,日夜不辍辛勤临摹奇峰名石百余方,收录有关雅石的诗文,终成洋洋四卷的《素园石谱》,使许多听代的名石得以流传于世。 当时奇石的观赏和收藏有三个新的动向:一是前朝留下的雅石大量流人古玩市场,进人古董之列;二是作家学者编著了较多的奇石谱录;三是皇家藏石、赏石成为“主流派”。 明代名士米万钟继承了先祖米芾的衣钵,也是一位石痴,他的三座别墅都以奇峰怪石而执京城之牛耳。他收藏的赏石有的是他祖上的遗物,有的是亲自收集的名石;如痴如醉地收藏,甚至达到倾家荡产的程度。有个故事是有关他“家道败落”的:一次,他在北京市房山县相中一块巨大的园林石,倾其所有还往京城米氏勺园,终因家资耗尽而弃于良乡郊野。后来清乾隆皇帝获知,才由皇家出钱将其运,置于颐和园,并取名“青芝岫”,人称“败家石”。 由此可以看出,自魏晋南北朝在苑囿庭园中叠石造山、竖石成峰以来,石峰一直是庭园行家之所爱,它们认为庭园石峰应该是“全方位”的观赏石,即四而可观者为极品,三面可观者为上品,前后两面可观者为中品,一面可观者为末品。但正如宋人杜绾所云;“大抵只两面或三面,若四面者,百无一二”,可见极品是少之又少,所以历代甚为重视前朝留下的石峰。明清两代也有不少名石遗留到现代,如当时号称“江南三名石”的瑞云峰、玉玲珑和绉云修分别在苏州、上海和杭州。前两峰均属太湖石,唯绉云峰是英石,它们都以自已的传奇故事流传迄今。 此外,在一些著名的公园、私家园林、古刹都有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园林石。上海嘉定龙潭公园中有数块历代遗留的观赏石,“翥云峰”是明代御史赵洪范丢宫后从云南返回嘉定时走海道压仓运回的,大湖石“缀华峰”系清代一家六进士的廖家后代所遗,还有两块分别名为“沙漠之舟”和“醉石”的名石则是当地盐商世家张家自南宋以来所传。 从清采到民国时期,中国进人现代社会,虽然由于科学的发展对观赏石的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连年的战争和社会动荡,使包括观赏石文化在内的石文化在中国基本上处于衰败的境地。“文革”十年中,几乎所有文化形态的收藏和鉴赏都被之斥为封资修的“残渣余孽”,被贬为没落阶级的“低级趣味”。但是国人潜意识中水永远没有也不会排斥观赏石文化这朵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葩;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观赏石文化的兴起就是明证。 5、改革开放一一一观赏石文化新的发展时期 20世纪20——30年代,近代科学之风强劲地吹进中华大地中国早期的学者竭力提倡“科学救国”,将西方的科学文化介绍给国人。在地球科学方而,许多学者起到了中国地质事业和地学教育事业的开拓作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是勇敢的拓荒者。章鸿钊先生于年著《石雅》,出版后大受欢迎,随后重印数次。 半个多世纪以来,与观赏石有关的学科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在结晶矿物学方而,引进了一些新方法、新仪器,中国科学家发现了数十种新矿物。岩石学、古生物学和陨石学方面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不少地质专业人士与全国石友道,参与了观赏石的理论研究。年,袁奎荣与邹进福等编著出版了《中国观赏石》随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地学家、藏石家和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观赏石的成因和鉴赏的许多实践和理论问题。年美学家王朝闻从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观赏石的美学特征,出版了《石道因缘》一书。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对观赏石的爱好一浪高过一浪。从20世纪80代初的小型石展到21世纪的几次大型和国际性石展,从“散兵游勇”到全国、省(区、市)观赏石协会的成立,到组织不同级别的奇石展、学术研讨会,以及学术性与观赏性期刊的出版,观赏石市场逐渐得到整合和发展,给人一种“风起云涌”的感觉。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提高,对美的追求,以及对科学文化的需求,促进了观赏石文化的普及和提高;观赏石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部件”。人的品格潜移默化的熏陶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构成了一曲优美而浑厚的和谐进行曲。 观赏石文化深深地渗透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奇石收藏和石饰已成为现代文化生活的部分,不论是专家教授、公务员、教师、公司的白领阶层,还是农民、普通市民,观赏石爱好者几乎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研讨会上教师与市民一起探讨赏石的鉴评标准,奇石擂台赛上,刚刚退出军旅生涯的将军与农民收藏家“同台献艺”。“石饰”作为石义化的体现.正逐渐与城市、街道、机关、学校,以至家庭装饰联系在一起。全国奇石爱好者达到二三万人,觅石、藏石、赏石、玩石和石文化的群众性团体千余个,赏石刊物一百多种,互联网上观赏石科普网站、网页和专栏联结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至通达世界的每个角落。观赏石登上了互联网的高速信息平台。 与大陆仅一水之隔的中国台湾,虽处海峡一隅,地域逼仄,但挽近时期的地质构造运动活跃,赏石资源十分丰富。著名的有台东的西瓜石、基隆的黄蜡石、花莲的玫瑰石、南田的图纹石,以及各种景观石、云母石、山溪石、风化石等等,近年来与大陆的交往更丰富了岛内的观赏石收藏。 台湾的赏石活动滥觞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不过当时的赏石活动与盆树艺术“合二为一”,观赏石与盆景一起举办展览会。随后,赏石活动日渐兴盛。据台湾石友说,年是台湾赏石艺术的转折点,从此雅石与盆树艺术“分而治之”,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岛内有中华观赏石文化协会、中华雅石会、春秋雅石会等百余个群众性赏石组织,迄今已有赏石者二三十之众。他们称观赏石为雅石,并将终分为景观石、象形石、图案石、抽象石、色彩石和奇石六大类。他们提倡素、简、朴和雅的赏石观和形意交融的“石人合一”观。近年两岸石友经常互访,互通有无。台湾石展和家庭雅石摆设给大陆石友留下了“小家碧玉”式的深刻印象。他们借柔道和围棋的段级划分方法,将赏石水平分为“五道段次”:石道社级(趣味观)、石道二段(美术观)、石道三段(道德观)、石道四段(抽象观)和石道五段(哲学观)。 (图文来源网络,感恩作者分享)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erfenga.com/nefxgpw/8310.html
- 上一篇文章: 你知道什麼是賀年十大油器嗎
- 下一篇文章: 刚刚江西又多了一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