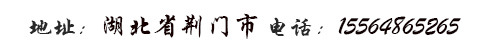周德梅过年
|
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间医院效果最好 https://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过年 ——我的童年之年 文/周德梅 过年的乐趣在于所有的筹备与等待,这筹备和等待总要提前一个来月。进到腊月,各家杀猪的杀猪,杀鸡的杀鸡,泡糯米的泡糯米。猪虽不是每家都杀得起,但腊肉总是要腌的,香肠总是要灌的,杀猪的人家都是提前预约了买主,东家十斤,西家八斤,南家十五斤或者二十斤,也有家境殷实的,两家合杀一头猪。鸡是家家都杀得起的,连我们这样的穷家都会杀上十只八只。杀鸡的日子,祖母在灶下大锅里烧水,我们兄妹拿着鸡罩捉鸡,扣在鸡罩里的鸡抱过去给母亲宰,满院疯狂逃窜的鸡片刻就拍翅蹬腿躺在了柿树下,几天之后又开膛剖肚地挂在了屋檐下,旁边傍着腊肉和香肠。糯米泡酥了,父亲在柿树下支起了石舂,边舂边用箩筛筛,雪样的细粉落在簸篮里,落不下去的粗颗粒倒回石舂里继续磕砸。磕糯米的那一两天,父亲连棉袄都不用穿的,真是麻利又强壮,有时候,他会在柿树下耍一套“流星拳”,那拳路是两个下放学生教给他的,真是疾如流星啊。母亲接来姥姥,来给我们一家人套棉衣,大人旧的棉袄棉裤拆洗后,重新套上旧棉坯,小孩的换上新棉花。小孩子长得快,旧的棉衣不是短了裤腿和袖子,就是露出了棉絮,拆洗过后总要接上一截才行。有时候,母亲会将自己压箱底的旧衣服翻出来给我们做袄里和袄面,天蓝色的士林布,红底黄花的灯芯绒,姥姥比划着那些衣服,抬起头征询祖母的意见:“太旧了,打个反吧?”“恩,反面鲜亮些!”祖母点着头说。于是,反面当成了正面,棉袄好象用新布做的,带着点磨砂的质感。我穿着天蓝色的新棉袄在檐前走,大黄狗扑上来就咬,我兴奋地抱住了它的脖子:连它也不认识我了呀!哥哥做了一件灰色的棉大衣,是父亲的旧衣服改的,他穿上后非常得意,雄赳赳地到处给人看:“瞧我的涤卡呢大衣!”“哇,涤卡呢大衣啊?咋和我的涤卡不一样呢?”“我的是涤卡‘呢’大衣!”他重重地说着“呢”字,不屑地扭着脖子,为别人的孤陋寡闻。母亲就着煤油灯做新鞋,黑色灯心绒是哥哥的,我和妹妹是黑色平布的,鞋头上绣花,花样是四奶奶剪的,我抢先将梅花的花样贴在自己的鞋面上,挑出桃红水红的丝线让母亲给我绣,剩下一对叶子样的花样妹妹也不喜欢:“我也要花!”母亲劝她:“这青叶子多好看呐,青枝绿叶多舒展!”“我要大花!”“你的脚小啊,大花你的鞋面上都放不下,这是竹叶,跟你的名字是一样的,是专为你的,谁也别想绣了你的!”为了一家人过年能穿上新鞋,母亲连天加夜地赶呀赶,新糊的鞋帮焐在身下,睡一觉就焐成了干的,又可以飞针走线了。每日里看着母亲做鞋的进度,转眼就看到腊月中了,腊中要扫尘,“要想发,扫十八,要想有,扫十九“,十八十九扫尘日,父亲穿着一身破衣服,戴着一顶破草帽,用绑了竹竿的扫帚,将墙壁、屋顶、廊檐底下的灰尘和蛛网掸扫下来,扫下的灰尘倒在村口的十字路口上,跟别家的作比较:“你家的粪堆真大啊。”“是的,今年的粪堆不小,你家的可不大呦。”“是啊,扫来扫去就扫了这么点尘,明年的庄稼没有肥料喽。”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庄稼人的粪堆是非常重要的,扫尘日的尘土被象征成了来年的肥料堆。屋檐上有融雪挂下的冰凌,挂得很长很长,出来进去,都快戳到了头顶上,我们拿着棍子去打,祖母跑出来制止,说打不得,说那是来年的麦穗,越长越好。父亲也不让打,他说打坏了屋檐,屋顶上的麦秸刚刚换过,屋檐簇新簇新的,厚厚实实平平展展,麦秸是向五爷爷家借的,来年收麦后得论斤还给他。麦秸是收割后的麦子没有经过碾压、用手摔打揉搓脱粒的麦秸,一根根金黄的还能站立的麦秸。沟里的冰被小孩子们用斧头砸开了,哥哥弄了一块搬回家来,折了一段麦秸放在冰上吹,冰很快被被吹出了一个小孔,穿进一根麻绳挂在屋檐下,明晃晃的,像一面锣,不能打麦穗的我们,就去打“锣”。“过祭灶,年来到”,祭灶那天吃祭灶糖,喷香喷香的麦芽糖,要用小锤子才能敲碎的糖坨子,一进到嘴里就软得化不开了,好象要把牙齿也粘掉,硬塞一块到母亲的嘴里,母亲立即皱起眉头说:“不好吃不好吃,甜死了!”那么好吃的“糖坨子”,大人都说不好吃。祭灶那天晚上,过年的第一挂鞭炮炸响,新年正式进入倒计时,厨房里上香点蜡,接受供奉的灶王爷,是灶台上的一张纸或者一幅小画,两旁写着两排小字:“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磕头祷告一番后,烧掉那张纸或那张画后,灶王爷就上天了,等到年后他会回来,灶台上重新贴一张纸或一幅小画,纸上是“东厨灶君之位”。祭灶过后准备蒸馍馍,两三盆的面总让祖母和母亲和上半夜,天气寒冷,面发得慢,面盆放在灶台上,灶底小心地加温,祖母会半夜起来看面添火,防止灶底太凉或太烫。二十六准时蒸馍,天不亮厨房就开动了,灶下的祖母,灶上的母亲,糖包子菜包子,花馍馍,蒸卷子,一整天厨房都是不熄火的,窜进窜出的我们,每笼馍出锅都要吃一个,一整天肚子撑得溜圆。妹妹躺在烧火的祖母怀里唱着歌:“推一锯,拉一箩,一把麦子磨不着,俺问姥家借呢个,姥姥不搁家,惹得妗妗咕啦啦……”还唱:“小板凳,凹凹腰,娶个新娘没好高,搁屋里老鼠咬,搁外头老鹰叼,去洗衣裳,跟癞猴(癞蛤蟆)俩扳一跤。”“二十七洗金蹄,二十八洗邋遢”,二十七那天,每家都烧水泡脚,郑重其事的劲儿,让心都缩紧了,年真的要来了。二十八或二十九是赶集的日子,父亲请回“家神”,买来瓜子、花生、红纸、门签、年画,还有大个的胖头鲢鱼。鞭炮在祭灶前就准备好了,“家神”挂在堂屋正中,是一幅画,或一幅字:天地国亲师位。年画中有给白娘娘戴花的许仙,有对镜簪花黄的花木兰,有草桥结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有共读《西厢》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花木兰最好看,粉红色的袖子短而飘逸,皓腕上戴着一只绿手镯。我觉得我家的年画比不上隔壁太太家的,她家有《红线盗盒》,有《昭君出塞》,昭君戴的帽子上还有毛毛,妹妹戴的帽子上也有毛毛,还有眼睛和耳朵,是只兔子,但比昭君的帽子好看差远了。最喜欢太太家的一幅《舞剑》,舞剑的少女穿了一双带绒球的鞋,剑柄上有长长的穗子,柔媚飘逸,学着她的样儿,我在鞭杆上也栓了穗子。红纸是用来写对联的,我家虽穷,但不欠债,所以对联并不急于贴,总要等到年三十的上午来贴。有人家欠债的,在腊月十几、二十几就贴上了对联,贴了对联就等于过年了,过年的时候是不能讨债的,这是规矩。而这年要过到正月十五才算完。对联是会计大伯写的,每年都有几幅字:“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门对青山龙虎地户朝绿水凤凰池”,三十的上午,祖母和母亲准备着年夜饭和饺子馅,我们帮着父亲贴春联,父亲贴大的,我们贴小的,父亲贴门窗,我们贴物件,有无数个“福”字等我们分派,倒着贴则是福到了,家里的器皿都是福到了,稻圈上则是“五谷丰登”,猪圈上是“六畜兴旺”。最后贴上五色的剪纸门签,家就全变了,新崭崭,红彤彤,喜洋洋,所有等待的快乐在这一刻达到了极致,真想拿根绳子将日头栓住,永远也不要过去,这天。天还亮着呢,不知谁家放响了第一挂鞭炮,接着一家两家,陆续响起来。祖母和母亲嬉笑着加快了动作,哥哥冲出去,一家一家追看放鞭炮,捡拾炸落的哑炮,一圈转回来,口袋里塞满了,手里还捧着两个圆子,说四娘娘家已经过年了,圆子是四娘娘给的。母亲看一眼他手上的圆子,突然惊呼:“你袄子咋啦,怎的这么大洞?”说着伸手要打,哥哥讪笑着跑开说:“炮仗炸的,装进口袋里又炸开了,明早穿新的!”我们的年夜饭终于好了,母亲令我和哥哥先去喂牛,哥哥端着一盆米饭,我举着一根麻秸火,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到会计大伯家,我们两家合着一头牛,他们看见我们来喂牛了,也赶紧端出了米饭来,跟我们一起端到牛头前。“犁一千,耙一万,年晚黑一顿饭。”这也是规矩。洗脸、净手、焚香,点蜡,鞭炮挑在竹竿上,哥哥举着,父亲拿着香烟去点,我们捂着耳朵倚门观看,看它炸开了花,属于我们家的年到了!菜色十全十美,在等待的日子里,想着这些菜,都会流出口水来,真正来吃的时候,好象已经“饱年”了。我和哥哥分喝着一瓶果子露,喝了一半时,哥哥说:“大妹,留点喝吧?一下子喝完没意思。”“恩”,我同意了,将“酒”收进柜子里。(第二天我请哥哥来分喝时,他摇头拒绝:“我不想喝,你喝吧。”我突然发现酒色变成了淡红,一尝,果然是水,大哭了一场。)吃完饭,给大人磕头拿压岁钱,祖母父母共九个头,拿到的是红色的一毛,还是绿色的二毛?父亲让我们去摸猪槽,我和哥哥不去,妹妹去摸了,结果摸到了一块钱,我们的眼睛都绿了。母亲命令哥哥到院中去抱“椿树王”,一边抱还要一边叨咕:“椿树王,椿树王,我长高嘞你长长,我长高,做栋梁,你长长,做嫁妆!”这是哥哥每年过年的保留节目,也是他的耻辱节目。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会偷喝果子露,对抱着“椿树王”的他,还略有同情,并且对自己长得太快有些过意不去。我攀在父亲的膝盖上,父亲问我:“你长得排场(漂亮)吗?”“排场!”“有多排场?”“驴脸挂大腮!”父亲笑了,祖母笑出了声。父亲告诉过我,“驴脸挂大腮”是最排场的,我认为我就是最排场的,当然非“驴脸挂大腮”莫属了,后来,后来“驴脸挂大腮”成了我的外号,哥哥叫的。雪依然在落,院中挖着壕沟一样的通道,积起的雪,高到了我们胸口。父亲找来树根树枝,搬进堂屋点起了火,一边守岁,一边讲故事,父亲讲的是千篇一律的《三国演义》,妹妹终于熬不住,睡在了他的手臂里。树根哔哔剥剥地响着,屋里很温暖。祖母和母亲在包饺子,我和哥哥在火堆里爆玉米花吃,扔进去一粒玉米,少顷,它就会“噗”地一声弹出来,开了花。哥哥将雪盛在“歪歪蜜”(蛤蜊油)的贝壳盒子里,放在火盆里烧,不一会儿雪水也开了,咕嘟咕嘟地冒开了水汽,“噗”一声,一粒玉米花也蹦了起来。夜深了,鞭炮声稀稀落落,渐渐停歇,祖母和母亲忙好了所有的事情,哥哥也去睡觉了。黑暗中,我拿着我的绣花鞋爬到了床上,从枕头下掏出新袜子往脚上套,尼龙袜子在黑暗中拉扯出火星一样的光,这是我最后的快乐,曲终人散后的快乐,这快乐闪着星星一样的光。我穿上绣花鞋,美美地在被窝里躺下,我纤巧端正的脚感觉着新鞋的板正与柔软,那么实在与真切。一件衣服被我蹬得滑落着,终于滑到地上,我没有起来去捡,我知道那不是我的衣服,那是哥哥的“涤卡呢大衣”......作者 周德梅 寿县作协会员 刊头书法丨黄先舜 寿州文艺编辑部 主编│王晓珂 副主编│金茂举聂浩涂德轩 编辑部主任│黄锐 常务理事│牛玉革葛厚远曹燕张宇王群 编辑部成员│许之格李军泽陶标杨华成胡三虎刘慧新朱公荣张进鲍润 摄影编辑│王玉明宋桂全许珍杨静 写出你的故事、写出你的精彩,这里是你自由自在的蓝天,任你飞翔!欢迎你的来稿: 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erfenga.com/nefsltx/8314.html
- 上一篇文章: 中药知识必学牛蒡子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