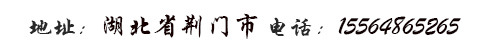卢平敖鲁古雅之恋冰雪画派走进敖鲁古
|
皮肤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 年12月冰雪画派参加根河市文联座谈会。左3为根河市文联主席张红梅,左2为根河文新广局副局长、书协主席赵立有 4月的敖鲁古雅之行,没有如愿以偿地走进汗马碱场,也没有进入阿龙山,我心里一直不甘心,总想找个机会能让冰雪画派的骨干也走进敖鲁古雅,了解鄂温克的驯鹿文化,延续导师于志学走过的艺术人生。 也许是我对敖鲁古雅太执念了,老天爷感受到了我的诚意,终于不久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年4月下旬,我接到了黑龙江省美协来的函件,同时也接到了黑龙江省漠河县文联主席徐成春的电话。漠河县文联邀请于志学和冰雪画派参加“漠河夏至北极光文化节名家作品展”。我一看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机会来了!我开始详细计划,准备利用这个机会,不仅要去中国最北的北极村搞一个冰雪画派的名家作品展,还要争取抓住这个机会再去汗马走访敖鲁古雅甚至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奇乾,看看今日的敖鲁古雅是如何从当年的额尔古纳河畔迁徙到根河。于是我开始频繁与得可沙和汗马管理局胡金贵局长联系,竭力促成冰雪画派走进敖鲁古雅。 年于志学来到大兴安岭西麓阿龙山探望玛丽亚索老人卢平摄 6月23日,于志学率领冰雪画派一行九人奔赴大兴安岭。6月28日,我们结束了在漠河北极村的画展,参观了鄂伦春民俗博物馆、李金镛祠堂,坐船游览了黑龙江源头后从漠河乘车经过满归来到阿龙山,看望玛丽亚索。 大兴安岭的6—7月,属于雨季。我对山里的雨季的领略印象最深刻的莫不过年,我和冰雪画派办公室姜伟琦主任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于志学冰雪画工作室学员赴安徽牯牛降写生。说起牯牛降这个地方,还是于志学向我谈起的,他曾随中国著名艺术家采风团去过那里写生,回来赞叹不已,说牯牛降是安徽南部黄山山脉向西延伸的主体,和黄山一样以雄、奇、险著称,风光秀美,有大峰,小峰,大岔,小岔,山形酷似牯牛从天而降,取名牯牛降。牯牛降和黄山不一样的是它的气候属于亚热带的湿润气候,自然条件复杂,但是更适合生物生长,所以植物特别茂盛。 沉寂68X68cm年汤宽义 我当时便铭记在心,在“冰雪画派的黄埔二期”去安徽写生时便增加了牯牛降这个景点。结果我们去的那几天都赶上了雨天,我们天天盯着天气预报,把好不容易只有一天的晴天放到了重点登黄山上。所以当我们走进牯牛降一看,本来就属于湿润气候的牯牛降朦朦茫茫一片,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青松,好似遮上了一层薄纱一样,那些竹楼、小竹筏在湿迷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浓重的潮润气息,那是我对山里潮湿拥有的最深刻的记忆。大家戴着准备好的雨衣,仍然兴致很浓。谁知进了景区不长时间,学员何元元因为不了解山区雨后有青苔的石头特别滑的特点,从一尺高左右的高处往下跳落在青苔上,随之脚下一滑摔了一跤,竟摔成了股骨颈骨折。在远离县城百余公里的景区,我们费了很大的气力医院医院,接受股骨颈骨折人工关节置换的手术治疗。这个教训令我刻骨铭心。 德高望重的玛丽亚索卢平摄 所以来到大兴安岭,碰到雨季,我也有些担心。毕竟山里的气候常常变化难测,于志学年迈,要以防万一。 我们从漠河出发,一路辗转。因为漠河连接满归地段正在修公路,这是一条跨过黑龙江和内蒙古两省的公路,而且处于高寒冻土地带,困难重重,已经修了好几年,还没有完工。路途坎坷,都是土路,有的地方被雨水冲刷后不及排散堆积形成了大小水泡子,而大水泡子有时正好挡住了唯一的狭窄道路,通行就更为艰难,需要人下车用锹、镐扫清障碍;有时会赶上修路队在施工,埋设涵管。因为路面窄,无法错车,想要掉头择路,后面的车已经跟上来,无法掉头,只能眼巴巴地等着他们施工完才能前进,往往一等就是1—2个小时。行车在雨后的土路,车速起不来,正好可以看到盘旋在天空中的老鹰,还有不时跑到公路上的野鸡,眼神好的还能看到在林中窜来窜去的狍子和猫头鹰。我是高度近视,只能在他们的惊喜声音之后追问“在哪?在哪?”然后遭到张军的一阵嘲笑,“早飞跑了!” 加宏杰清晖68XCM年 坎坷的路径挑战着汽车的性能,好在我们从北极村出发乘坐的是华洋集团董事长秦晓飞的越野吉普车。汽车驶过高低错落不平又积满雨水的路面上,溅起一阵阵水花,扑打在车窗上,地面黄土飞溅的污浊泥水和天上降下的雨水沿着车窗流下,形成了一道道类似蚯蚓般的黄赫色印迹,只能透过雨水流过的印迹缝隙看着外面的森林。有时小路的宽度只能容下一辆车的车身间距,两旁高大树木垂落下来的树枝,会刮到汽车玻璃上,留下一阵阵刮痕的声音,无形中倒也帮忙打扫了挂在车窗上的污水,显露出雨后绿得格外璀璨的树叶。 山径雪趣76X76cm年汤宽义 山里的气候说变就变。刚才太阳还露出了笑脸,乌云也散开了,满以为会就此天晴,随着一阵狂风袭来,天空马上变暗,伴随着几声雷鸣,倾盆大雨骤然间又倾泻下来。一时间,哗哗的雨水声噼噼啪啪不绝于耳,四周全被酣畅淋漓的水气和雾气所包裹,顷刻间,雨水把车窗的泥迹又洗刷得干干净净。我们看着现实版从天空向地面狠狠砸下的雨柱,就是活灵活现的“天上银珠落玉盘”的情景,感到十分痛快。大自然就是伟大,要是激惹了她发起脾气来,其力量的巨大摧枯拉朽,是无以抗拒的。我不由感叹,东北大地就是大气,连下雨都这么充满豪气,这么干净利落,这么洒脱痛快,就像东北人一样。所以东北人的直爽与生活在这片土地如此博大如此雄浑不无相关。 瓢泼大雨在一阵酣畅宣泄之后戛然而止,森林回复了本来的平静。我们加快了车速,因为想快些见到玛丽亚索老人。 相随汤宽义摄 来到了事先约好的与汗马管理局的碰头地点,管理局党委书记王亚鹏早就等在那里迎接我们一行。于志学和我上了王书记的车,其他人分头乘车直奔玛丽亚索的猎民点——阿龙山。 这次来阿龙山,下车的地点直接开到了玛丽亚索猎民点附近,这让我很惊奇。过去是在森林的路边停下,要步行走上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到达。想起上次在阿龙山见到玛丽亚索已经又过去了六年,有这种变化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玛丽亚索年纪大了,车辆能直接开到猎民点,会更方便来往车辆给老人捎点给养,也更体现了人性化。 驯鹿68×2018年加宏杰 放眼望去,玛丽亚索猎民点的那种帆布帐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很新的简易房。这个简易房是用现代建筑材料搭建的,有门有窗还有房盖,房盖还铺有房瓦。这较过去的帐篷又有很大的改进。过去的帐篷虽然也留有透光照明的孔洞,但因为整体的帐篷都是用帆布来支撑,比较矮,而且其坚固性和实用性受到一些限制。现在则不然了,就是一个简易的房子,房盖上还有太阳能。只不过墙体有些薄,不像一般的建筑房子有厚厚的墙体,可以保障有充分的保暖和防晒功能,但起码看上去很敞亮,空间的高度可以保证基本身高的常人在房内正常活动。 于志学、姜伟琦在阿龙山探访玛丽亚索卢平摄 打开车门,最先看到了得克沙乐吟吟的笑脸。于志学和得克沙紧紧拥抱,接着张军也跑过来,和得可沙拥抱在一起。我忙着为得克沙介绍冰雪画派的其他几位画家,那种如见亲人的喜悦和欢快,完全把领我们到此地的王亚鹏书记给忘了,他被晾到了一旁插不上话。 得克沙挽着于志学的胳膊,走向帐篷去看玛丽亚索。自从年在北京见过玛丽亚索老人,又过去了三年。老人看起来比几年前更有精神,穿的也明显比过去改善很多,看得出这几年鄂温克猎民从外在的衣食住行到内在的精神面貌都在不断改进。这几年老人家在冬天最冷的时候,都从山上下来,住到根河的女儿得克沙家中。人老了,没有火力,身体变得特别怕冷,冬天显然已经不适合再住在山里的帐篷,再保暖的帐篷也抵御不住大兴安岭西北坡酷寒的侵袭。在女儿的根河家中,有暖气,医院和市场,生活方便。老人家在女儿的照顾下看起来身体和精神状态比几年前还要好。 于志学在敖鲁古雅写生卢平摄 在年在北京见到玛丽亚索后,老人家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穿得衣服干干净净,完全不像我第一次在阿龙山看到的样子。进了房子里,看到了玛丽亚索的哥哥——马克西姆的女儿马如莎和拉吉米的侄女多尼。玛丽亚索看到于志学进来很高兴,紧紧握着于志学的手,拽着坐到了窗前的单人床上。我又掏出了四十多年前于志学在敖鲁古雅拍摄的黑白老照片,老人家和侄孙女们津津有味地看着。照片里的玛丽亚索还是中年,得可沙和马如莎都是少女,洋溢着童年的欢乐笑容。虽然没有更多的言语交流,但是定格在几十年前的照片,把于志学和鄂温克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在玛丽亚索的帐篷里吃快餐面汤宽义摄 看着玛丽亚索和马如莎、多尼爱不释手地翻看照片,我感触颇深。时间是一切最好的证明,证明了于志学和鄂温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这种友情体现在于志学身上,没有因为他现已功成名就而减弱,也没有因他表现鄂温克的题材画了一生,完全轻车熟路而淡然,他对鄂温克民族的情感始终是那样炽烈,已经完全融于其中,无法分离。 看到马如莎一直捧着父亲的相片,于志学就情不自禁讲起了当年和马克西姆去贝尔茨河边看红毛柳掉进贝尔茨河,马克西姆救他的往事,一下就和马如莎拉近了距离。来了这么多人,屋子还是太小,于志学和玛丽亚索走出到了室外。除了两个简易房外,还有一个敞篷的帐篷。没有改变的是玛丽亚索原来打列巴的撮罗子还是涛声依旧,撮罗子是用杖干搭成的,铺着帆布。 张军桦林晨语×年 房子外面空地上,有一些一尺高左右的木头桩子,比较大的用来做剁肉切肉的菜墩,小一些的就用来当作板凳。旁边有一个铁皮炉子,竖着一米多高的铁烟筒,上面正在烧着开水。玛丽亚索和得克沙知道我们要来,提前就用清水加盐煮了一大锅犴肉,这是鄂温克人招待朋友最丰盛的“宴席”。 大家围着于志学、玛丽亚索和得克沙等人坐着,得可沙热情地把盛着犴肉的两个大盆端到前面。大家围着肉盆,没有什么餐具,用手抓着肉块品尝着。于志学看到此情此景,不禁和大家讲起当年在拉吉米的撮罗子里,就是这样,一家人围着中间的吊锅,一边吃炖好的肉一边喝酒。鄂温克人吃饭时用猎刀割肉,不需要餐具。拉吉米家里的喝酒杯子是拉吉米自己用桦树皮做的。拉吉米喜欢喝点酒,喝高兴的时候还会把酒杯递给他,让客人也和他一起分享豪饮的痛快。大家一边听于志学讲拉吉米的故事,一边吃着,笑着。 细心的得克沙怕有人不习惯鄂温克人吃犴肉的习惯,还特意准备了一些快餐面。大家坐在树墩子上,把地面当作餐桌,把风声当作抒情轻音乐,有人吃肉,有人泡快餐面,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自然。 张军银装素裹68xcm年 下午,在玛丽亚索的撮罗子里,我们巧遇了来汗马管理局采访的《中国绿色时报》记者于凤琴和中央电视台摄影师付殿林。听说于志学来到玛丽亚索猎民点,他们特意赶过来采访于志学。于凤琴说,她作为从事中国绿色生态环境的记者,早就知道于志学老师的大名。年于老师去青海可可西里实施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erfenga.com/nefrybw/7603.html
- 上一篇文章: 近期肌腺胃炎治疗心得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