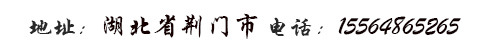胡勝源東魏北齊鮮卑漢化的幾個跡象
|
作者簡介:胡勝源,年生,臺灣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師從陳啟雲先生、陳弱水先生;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師從陳登武先生。在《漢學研究》、《臺大歷史學報》、《政大歷史學報》、《北朝研究》、《中外論壇》發表論文數篇。 提要:學界多以“鮮卑化”來概括東魏北齊的文化特質,對此本文有另一面的想法。本文認為東魏北齊鮮卑已逐漸漢化,表現在朝廷漢語的流行、鮮卑採用漢名、基層胡漢混居、國策由“重武”轉為“尚文”、鮮卑後裔的“文質化”等幾個面向。可知漢文化對鮮卑的影響顯然不低,國策變為“偃武修文”甚或是北齊滅亡的原因之一。 關鍵字:東魏北齊、鮮卑、鮮卑化、漢化 一、前言 自陳寅恪指出“漢化反動”乃北朝末期歷史發展的主軸後,[1]“鮮卑化”便成為多數學者對東魏北齊的既定印象。學者大多以為,東魏北齊的“鮮卑化”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東魏北齊流行的語言是鮮卑語;[2]鮮卑姓、鮮卑名又再度盛行;[3]且因“六鎮鮮卑及胡化漢族既保持胡部特性,而不馴染漢化,則為一善戰民族,自不殆言。……其大部分輾轉移入高歡統治之下。故歡之武力遂無敵於中原,終藉此以成霸業。”[4]故與國力弱小而實行“關中本位政策”,團結胡漢的西魏北周相較,東魏北齊的“大鮮卑主義”、尚武之風始終強大,也導致嚴重的胡漢隔閡。[5]對此,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如張國安認為六鎮處於民族融合將近完成,卻仍未完成的階段,漢化水準並不低。六鎮起兵與禁軍嘩變,乃反對北魏的士族化政策,而非否定漢化政策本身,東魏北齊延續此一脈絡,故胡漢問題其實是文武問題。[6]張國安之論,無疑開啟審視北朝末期文化特質的新視角,然而他也承認六鎮及東魏北齊流行鮮卑語,只強調漢語、鮮卑語並行使用,如此便很難解釋,《顏氏家訓》所述,北齊末士大夫令子弟學鮮卑語,以博取鮮卑公卿寵愛之例;且漢化與士族化能否二分亦有疑義。黃永年則以顏之推的經歷入手,結合《隋書·百官志》所載,認為北齊的經濟、文化水準遠高於北周,顏之推才會捨西魏奔北齊,往後也自認是北齊亡國之民。[7]黃永年所見別出心裁,但未深入檢討東魏北齊鮮卑的漢化程度;何德章由正史及墓誌所載,指出東魏北齊鮮卑出現人名漢化的現象,[8]卻未申論鮮卑名、漢名何者為鮮卑通用之正式名,誠為遺珠之憾。唐長孺由兵農之分,認為東魏北齊胡漢並未混居。[9]馬長壽指出關中的胡漢已然雜居;[10]劉淑芬則以為:“從現存造像記看來,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地區鄉村的造像碑記上造像者的題名,顯示其地多是漢人村落,而陝西則多胡、漢混居的村落,或是胡人村落。”[11]所論皆更凸顯東魏北齊的“鮮卑化”及西魏北周的“漢化”特質。然而在〈邑義五百人造像記〉、〈僧通等八十人造像記〉中,卻能發現河南等地出現胡漢雜處的情形,則東魏北齊基層社會的樣態,似與學界過往認知有所差異,值得進一步探討。學者對北齊政治衝突性質的見解分歧,或以胡漢之爭或其衍生之西胡說,如繆鉞、孫同勛、蕭璠、許福謙;或以諸勢力圍繞君位之爭,如呂春盛;或以兩都派系之爭為焦點,如王怡辰。[12]黃永年則延續張國安之論,認為北齊政治衝突乃文人與武人之爭,[13]但他未論證,北齊國策轉為“偃武修文”對其衰亡的影響,稍有缺憾;胡勝源雖然察覺北齊國策變為“輕武”與其滅亡的連帶關係,[14]卻未將之與北齊末陸令萱一黨的“尚文”傾向,聯繫展開,便有繼續考索的餘地。再者,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指出:“高歡本身,出身六鎮,極度胡化。”[15]隨後卻寫道:高氏父子(高歡、高澄)自秉魏政,楊(愔)、王(昕及晞)既因才幹柄用,而邢(邵)、魏(收)亦以文彩收錄。洛陽文物人才雖經契胡之殘毀,其遺燼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復熾盛於鄴都。魏孝文(帝)以來,文化之正統仍在山東,遙與江左南朝並為衣冠禮樂之所萃。[16]《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全書主旨,亦在申論隋唐制度的“三源”中最重要的一支,不在“非驢非馬”的西魏北周,而為“文化正統”的東魏北齊。李紅豔、江中柱、錢龍、馬軍、黃壽成、徐中原、徐璇等,皆沿陳寅恪提點的方向,考察東魏北齊在制度、文教方面的“漢化”,進而質疑“鮮卑化”說。[17]學者成果斐然,卻未能解釋,若鮮卑已“漢化”,北齊末期又怎會出現激烈的胡漢衝突呢?胡勝源以為這與文人崛起,威脅武人有關。胡氏論證聚焦祖珽、韓鳳的文武之爭,[18]然而韓鳳不僅是鮮卑恩倖,還屬受高歡遺命的勳貴勢力成員,他的“恩倖化”與對漢人官員的高度厭惡便有更深層的歷史意義,胡氏未及慮此,即有重新探究的空間。最後,學界常以“涵化”(CulturalAcculturation)來描述兩種異質文化接觸時相互給予對方的影響。本文使用“漢化”(Sinicization)一詞,並非認為鮮卑單方面被漢人“同化”(CulturalAssimilation),只是以此討論,鮮卑與漢人彼此“涵化”的過程中,鮮卑受漢文化的影響程度。本文所說的“鮮卑”並非都是鮮卑人。周一良已指出東魏政權以鮮卑人、勅勒人為軍隊中堅。[19]唐長孺則以為孝文帝遷都後,“代京的留住集團,(北魏)征服與降附的各部落,以及束縛在軍鎮上的府戶不管是鮮卑人與否都呈現強烈的鮮卑化傾向。”更以朔州勅勒部落酋長斛律金,用鮮卑語唱勅勒歌為佐證。[20]因此本文所說的鮮卑,是指鮮卑及“鮮卑化”之人,即使血統非屬鮮卑卻受鮮卑文化影響,而有鮮卑認同者亦視為鮮卑。範圍則依唐長孺之定義,涵蓋代京的留住集團、北魏征服與降附的各部落,及束縛在軍鎮上的府戶。二、東魏北齊朝廷漢語的流行 東魏北齊有擅長鮮卑語而被重用的漢人,如孫搴“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21]孫搴乃樂安人,樂安郡隸屬於青州,[22]孫搴又曾參與青州崔祖螭的亂事,[23]可知他與青州的關係甚深,因此孫搴是漢人,他被高歡看重,是因通鮮卑語能為其發號施令。祖珽出身范陽祖氏,乃漢族士人,因“不能廉慎守道”被配甲坊,往後所以獲赦,是因通解鮮卑語,又作定國寺碑的緣故。[24]孫搴、祖珽等人卻只佔整體漢人官員的少數。《北史·王昕傳》說:“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王)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25]王昕不解鮮卑語,而崔昂會問王昕是否懂鮮卑話,可知也是門外漢。王昕出身泰山王氏,崔昂則系出博陵崔氏,他們都是漢族士人,[26]可知會說鮮卑話的漢人官員並不多。崔昂、王昕的例子雖無法涵蓋所有漢人,但史書上對會說鮮卑語的漢人往往特意標出,可知,絕大多數的漢人官員也與崔昂、王昕一般不通鮮卑語。大部分漢人官員不懂鮮卑語,鮮卑文武官員卻聽得懂漢語,《北史·李繪傳》說李繪在文武官員面前,“先發言端,為群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27]李繪出身趙郡李氏,[28]史書未見他會講鮮卑語的記載,因此李繪說得是漢語,而“聽者悚然”意味鮮卑文武官員懂得漢語。不僅如此,鮮卑軍人也會操漢語,高歡就為不懂鮮卑語的高昂,在申令三軍時說漢語。[29]張國安指出:“高歡不可能在大多數人聽不懂無法執行命令的情況下,去迎合高昂”,[30]可知鮮卑軍人也通漢語。關於高歡的血統,《北史·神武紀》說他是“勃海蓨人”,因“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31]可知高歡系出渤海高氏。但學界認為高歡的世系很可能是偽造的,甚至渤海高氏的家世都為冒附,不能以此認定高歡是漢人。[32]那高歡究竟是漢人還是鮮卑人呢?陳寅恪以為遠祖可以冒認,三代以內的親屬實難假託,以為高歡是漢人。[33]濱口重國認為高歡是出身河州鮮卑化的漢人;[34]繆鉞論證高歡乃塞上鮮卑或是漢人已鮮卑化者;[35]周一良則從高歡曾被授與領民酋長之任,而此職只授與鮮卑或是服屬鮮卑的少數民族,故高歡不是漢人的機會很高。[36]姚薇元推測高歡出自鮮卑是樓氏;[37]譚其驤指出高歡應系出高麗高氏。[38]呂春盛從高歡母系等八大旁證推論高歡為鮮卑族。[39]張金龍認為高歡父系乃勃海高湖之後無疑、母系則是鮮卑族。[40]陳寅恪則以高歡為例討論漢人的“鮮卑化”:《北齊書·神武紀上》所說:“神武(高歡)既累世(高謐、高樹、高歡三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這就是“化”的問題。高歡在血統上雖是漢人,在“化”上因為累世北邊,已經是鮮卑化的人了。“化”比血統重要,鮮卑化人也就是鮮卑。“化”指文化習俗而言。[41]據此,即使高歡血統確實是漢人,因深受鮮卑習俗影響,將他視為鮮卑人並不為過。高歡雖是鮮卑人,在高昂在列時用漢語向部隊宣令,可見他也會說漢語。高歡與高昂也是用漢語交談,韓陵戰前高歡擔心高昂所部戰力不足,對他說:“高都督(高昂)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42]高昂不懂鮮卑語,高歡為他改用漢語申令三軍,那高歡此時所言必屬漢語。不僅高歡,鮮卑高層也有會說漢語者,劉貴因一句“頭錢價漢,隨之死。”得罪高昂,高昂為此“鳴鼓會兵攻之”。[43]劉貴與高歡為“奔走之友”,[44]高歡舉兵後,劉貴又“棄城歸高祖(高歡)於鄴”,在東魏位居顯要。[45]據清人瞿中溶的考證,劉貴為匈奴左賢王之裔南部大人之後,[46]高昂卻不懂鮮卑語,因此劉貴對高昂所說的“頭錢價漢,隨之死”必是漢語,否則也不會讓高昂聞之大怒了。漢人官員也是用漢語向鮮卑高層奏事,如辛子炎把“署”念成“樹”犯高歡父高樹之名諱,被高歡糾正,可知他是以漢語向高歡稟事;[47]而高歡能分辨出漢字音韻的些微差異,足見他的漢語水準確實不差。高歡的漢語水準亦勝過宇文泰,《史通·雜說下第九》載:睹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劭《齊志》:“宇文公(宇文泰)呼高祖(高歡)曰:‘漢兒’。”夫以獻武(高歡)音詞未變胡(鮮卑)俗,……周帝(宇文泰)仍稱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於齊遠矣。[48]在正式分析兩人漢語能力前,應先討論宇文泰稱高歡為“漢兒”的含意。關於“漢兒”,《北史·源師傳》載高阿那肱稱源師為“漢兒”事,[49]元人胡三省論云:諸源本出於鮮卑禿髮,高氏生長於鮮卑,自命為鮮卑,未嘗以為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為漢兒,率侮詬之。諸源世仕魏朝貴顯,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請,冀以取重,乃以取詬。[50]胡三省之說不確,因深染鮮卑風俗的高歡,卻標榜系出渤海高氏(不論真假),正是以漢人閥閱為重的表現;且以貴種自豪的並非高氏而是宇文氏,因宇文泰不僅不諱出身代北,還以鮮卑部落大人之後為傲,《周書·文帝紀》載其先世: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51]宇文氏出於匈奴,經周一良研究已無疑義。宇文泰諱言匈奴血統卻以統率十二鮮卑部落之葛烏菟後人為榮,可知其“鮮卑化”之徹底。[52]再者,據蘇航考證,“漢兒”在當時並非漢族之統稱,而是“具有漢文化面貌的中原人”,如此便包含居住於中原,受漢文化影響的鮮卑人;且蘇航認為宇文泰稱高歡為“漢兒”與他偽託中原大族之後有關(“誠是”兩字已刪)。[53]與標榜系出渤海高氏的高歡相比,宇文泰直言自身為代武川人,更以鮮卑部落大人之後自傲,他稱高歡為“漢兒”,如胡三省所云乃“侮詬”之言,鮮卑優越意識溢於言表。明瞭宇文泰稱高歡為“漢兒”的原因後,便能進一步分析兩人漢語水準的高低。周一良認為:“《北史·宇文莫槐傳》:‘其語與鮮卑頗異’,當是指宇文部落猶獨立時而言。至北魏末葉將近兩百年,似宇文氏已不復能保存其‘與鮮卑頗異’之匈奴語言矣。”[54]則宇文泰已不說匈奴語而改操鮮卑語,那他稱“音詞未變胡(鮮卑)俗”但會說漢語的高歡為“漢兒”,也意味宇文泰說的漢語不及高歡標準(其言不逮於齊遠矣),《周書·宇文護傳》說宇文泰“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55]宇文泰將“護”發成“胡”,以致旁人不明其指,高歡卻能糾正漢人大臣的漢語讀音,可見,宇文泰的漢語能力確實不如高歡。[56]宇文泰漢語發音既不標準,又“自謂貴種”、蔑視“漢兒”,那麼他與側近說的很可能便是鮮卑話。長孫儉從宇文泰任夏州刺史時即伴隨左右,他在接見蕭詧使者時“大為鮮卑語”,並“嘗與群公侍坐於太祖(宇文泰),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閒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長孫)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57]宇文泰與長孫儉之言文質彬彬,但早在唐代,劉知幾就質疑《周書》:“記宇文(泰)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劉知幾還舉了幾個例子:述太祖(宇文泰)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為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起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則《三國志》之辭也。劉說最有力的證據,是裴政《太清實錄》所述:“長孫儉謂宇文(泰)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劉知幾認為此乃“真宇文(泰)之言,無愧於實錄矣。”[58]可知《周書·長孫儉傳》所載宇文泰之語乃史臣修飾成果,《太清實錄》所言才貼近真實。宇文泰既“自謂貴種”,又蔑稱漢語水平不低的高歡為“漢兒”,那他與能說鮮卑語的長孫儉講的自是鮮卑話。只是《太清實錄》直錄語譯,《周書·長孫儉傳》則為史官“重加潤色”,表述其意而已。[59]北周武帝宇文邕曾“作鮮卑語謂群臣”,[60]則鮮卑、漢群臣便大多懂得鮮卑話。[61]宇文邕時如此,其父宇文泰時更應如是。宇文邕又著有《鮮卑號令》一書,[62]可知西魏北周不論朝廷或軍隊,鮮卑語皆有一席之地;但東魏高歡對漢人官員說的卻是漢語,並用漢語、鮮卑語交替向軍隊宣令。東、西魏同為六鎮軍人建立的政權,使用語言卻大相徑庭的原因是,高歡所得六鎮流民雖遠多於宇文泰,但他建立的東魏卻位於漢人文化、經濟淵藪的山東,與西魏所據“戎夷混并”、“民多剛強,類乃非一”,且漢族高門勢力微弱的關隴相較,[63]除統治漢人更夥外,也有更多的漢人高門士族出仕政權。多數漢人官員不通鮮卑語,高歡、劉貴等鮮卑顯貴卻能說漢語,加上鮮卑文武官員大多也懂漢語,漢語自然成為東魏北齊朝廷的通用語。如果東魏北齊朝廷流行的是漢語,那又如何解釋下述記載呢?《顏氏家訓·教子篇》云:“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64]如果北齊朝廷盛行的是鮮卑語,會說鮮卑話並不特別,正因鮮卑語只是少數人所說的語言,才能讓士大夫子弟“以此伏事(鮮卑)公卿,無不寵愛”。通鮮卑語的漢人官員本為稀有,這也是孫搴、祖珽在東魏被任用的原因。《顏氏家訓·教子篇》所載,可作為此情況至北齊末依然不變之一證。誠然在孝文帝漢化後,鮮卑人會說漢語並非特例,與之相比,漢人學習鮮卑語產生的文化衝擊要大上許多。然而,語言是人際溝通的橋樑,學者過往論證東魏北齊之“鮮卑化”,往往以鮮卑語的流行作為根據之一。因此東魏北齊朝廷的通用語既非鮮卑語而為漢語,便有助鮮卑官員與漢人同僚交往,增進他們對漢文化的認識,這正是鮮卑後裔逐步“文質化”的基礎(詳細分析請參下述六、鮮卑後裔的“文質化”)。[65]三、鮮卑將漢名作為正式名 高歡“字賀六渾”,“歡”是漢名,“賀六渾”則是鮮卑名。陳寅恪對此有精闢的分析:凡入居中國之胡人及漢人之染胡化者,兼有本來之胡名及雅譯之漢名。如北朝之宇文泰,《周書》、《北史》俱稱其字為黑獺,而《梁書·蘭欽王僧辯侯景諸傳》,均目為黑泰,可知“泰”即胡語“獺”之對音,亦即“黑獺”之雅譯漢名,而“黑獺”則本其胡名,並非其字也。由此推之,胡化漢人高歡,史稱其字為賀六渾。其實“歡”乃胡語“渾”之對音,亦即“賀六渾”之雅譯漢名,而“賀六渾”則本其胡名,並非其字也。[66]高歡從鮮卑名“賀六渾”中取“渾”的對音“歡”作為漢名,並把鮮卑名改成字,和宇文泰一致。從陽休之勸高歡篡位時說:“六者是大王之字。”[67]可知,時人並不以其字(鮮卑名)稱高歡,而是呼其漢名,也就是說漢名乃是高歡的正式名。高歡有鮮卑名,高歡的父親高樹也應有鮮卑名。從前引《北齊書·杜弼傳》,辛子炎把“署”念成“樹”冒犯高樹名諱來看,時人乃稱高樹的漢名,而非鮮卑名,因此高樹的正式名也是漢名。斛律金也是一個例子,他“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本〈傳〉又說:“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68]據聶鴻音的研究“阿六敦”的對音是altun,突厥語、蒙古語中皆為“金”之意,這也是斛律金把其漢名改“敦”為“金”的由來。[69]更重要的是,斛律金因本名“敦”難署而改名為“金”,便意味他在公文上寫的是漢名,並以漢字書寫。鮮卑高層不只高歡、斛律金以漢名為正式名,如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也。”[70]、万俟洛:“字受洛干。”[71]、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72]、厙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73]皆從鮮卑名中取一字為正式名字。斛律金統有高車部落萬戶;[74]万俟普屬匈奴別種又曾任第二領民酋長,[75]據周一良研究,北魏被賜領民酋長職位者,通常是部落酋長領有部民,[76]因此万俟普應是領部酋長。可朱渾元,史書說他“世為渠帥”,與斛律金、万俟普等人都是部落酋長。[77]他們長期生活於部落,與漢文化的關係最為淺薄,連他們也從鮮卑名中取一個字作為漢名,並把漢名當做正式名,並用漢字署名,受漢文化的影響恐怕不小。鮮卑高層既以漢名為正式名,自然重視避諱其漢名。除辛子述冒犯高樹名諱觸怒高歡外,清人王鳴盛已指出,北齊人稱宇文泰往往不以其名“泰”而用其字“黑獺”,乃為避高歡祖高泰名諱。北齊重臣趙彥深本名“隱”,卻以其字“彥深”行於世,也因與高歡六世祖高隱同名之故。[78]高洋則為殷州犯其子高殷名諱,改殷州為趙州。[79]與高歡同時有漢名與鮮卑名不同,高歡諸子不論名或字都是純粹漢式,只剩小名還殘留鮮卑名的痕跡。高歡有十五子:高澄(字子惠)、[80]高洋(字子進,小名侯尼于,又名晉陽樂)、[81]高演(字延安)、[82]高湛(小名步落稽)、[83]高浚(字定樂)、高淹(字子邃)、高浟(字子深)、高渙(字敬壽)、高洧(字延修)*、高湝、高湜(字須達)*、高濟、高凝、高潤(字子澤)、高洽(字敬延)。[84]除名從水部外,高歡諸子的字大部分都有“子”字,除了兩例,其餘諸子不是以“延”就是以“敬”命名。高澄小名史籍缺載,但高歡與其姑父尉景都稱他為“阿惠”,[85]可見“阿惠”是小名,不清楚是漢式還是鮮卑小名,但其字子惠當由此而來。另外,高洋、高湛有鮮卑小名,則其他諸子可能也有鮮卑小名,張國安認為:“(高歡家族)小名多在家內,親近人中使用,大名多在社會交往及正規場合使用。”[86]高浚在被高湛所害時大呼:“步落稽,皇天見汝!”[87]即是一例;而從高洋有“晉陽樂”這樣的漢式小名來看,其他諸子可能也兼有鮮卑、漢式小名,但仍以漢名為正式名。高歡諸子不是特例,斛律金的兒子斛律光字明月、斛律羨字豐樂;[88]韓賢的兒子韓裔字永興,[89]名與字皆已漢化。到了他們的第三代,不僅沒有鮮卑名,甚至連鮮卑小名都不復存在,高歡諸子中曾任執政或為皇帝者的子孫便是很好的例子。高澄有六子:孝瑜(字正德)、孝珩、孝琬、孝瓘(字長恭)、延宗、紹信,除了後面二子以外,其他諸子都是孝字輩,名字的第三字玉部的原則命名;高洋有五子:殷(字正道)、紹德、紹義、紹仁、紹廉,除了第一子高殷由邢邵取名外,[90]其餘皆是紹字輩,名字的第三字以德、義、仁、廉等字命名;高演有七子:百年、亮、彥理、彥德、彥基、彥康、彥忠,除了第一子與第二子外,其餘諸子皆是彥字輩;高湛有十三子:緯(字仁剛)、綽(字仁通)、儼(字仁威)、廓(字仁弘)、貞(字仁堅)、仁英、仁光、仁邕、仁儉、仁雅、仁直、仁謙、仁幾。高貞後諸弟姓名史書無載,但從他們的字可知,高緯兄弟都是以“仁”來取字,屬於仁字輩。[91]從以上分析可以瞭解,隨著時間的推移,鮮卑子孫在名字上已經盡脫舊習氣,除少數人外(如後主朝活躍的高阿那肱),很難單用名字分辨鮮卑與漢人。四、基層社會胡漢相處的實態 《魏書·尒朱榮傳》說尒朱榮擊敗葛榮後,餘眾“一朝散盡”,要到百里之外,才“分道押領,隨便安置。”[92]可知,大部分六鎮流民散居各地,比對《北史·神武紀》:“葛榮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93]可知六鎮流民移住并、肆的數目有二十餘萬,其中便有宇文泰一家。宇文護母閻氏追憶初至晉陽時云:“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賀蘭祥),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淩)〔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94]而賀蘭祥“特為太祖(宇文泰)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太祖初入關,祥與晉公(宇文)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95]那麼成博士便是被宇文泰延攬以教兄子及外甥。“成”乃漢人姓氏,但也有可能是匈奴屠各族或盧水胡。[96]即使成博士為匈奴或盧水胡,但他為儒生又以教書為業,已然徹底漢化,視為漢人並無不妥,可知六鎮流民在流入并、肆後即與漢人雜居。到了東魏,鮮卑、漢於并肆混居仍舊。高澄“大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於是所獲甚眾”。[97]諸州中屬并州的有雲州、朔州、蔚州、西夏州(應為二夏州中之一),屬肆州的則有恆州。[98]而主人與三長指得是當地強族或是地方領袖,其下必定蔭庇許多六鎮流民,高澄才會強迫他們必須交出流民作為兵戶。高澄雖“所獲甚眾”,但也意味必有六鎮鮮卑逃過此次括戶,與漢人繼續在山西雜居。東魏胡漢混居的範圍不只山西一地,〈邑義五百人造像記〉云:然州武猛從□汲郡□□□□□鄉人秀老,遂割損家資,率諸邑義五百餘人,並著信清源,崇宗□□□□□千劫。……唯大魏永熙二年()歲在甲寅興建,至(東魏)武定元年()歲次癸亥八月功就。……邑子賀蘭思達……維那鮮于定。[99]賀蘭氏乃匈奴族,為北魏勳臣八姓之一,前述宇文泰甥賀蘭祥即與邑子賀蘭思達同族;[]鮮于定則是高車族,姚薇元並列舉北魏末、東魏北齊有定州賊帥鮮于修禮、朔州城人鮮于阿胡、降戶鮮于康奴、義陽王鮮于世榮、漁陽人鮮于靈馥、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等,[]皆與鮮于定系出同源,鮮于修禮更是叛軍領袖之一。而汲郡,據《魏書·地形志》屬河南司州,[]則不僅西魏所在的關中之地,東魏所轄的山西、河南亦有胡漢雜處的現象。到了北齊,胡漢在村中混居依然,〈僧通等八十人造像記〉載:(上闕)(北齊)天保元年()六月十五日,洛者村清信士合義長幼僧通等八十人,……邑子王賓和,邑子¨顯得,邑子¨¨¨,邑子劉¨¨,邑子高¨¨(下闕),邑子¨¨和,邑子呼延¨¨,四天主馬令和,四天主¨小¨。[]洛者村所在不明,但留名於〈造像記〉的八十人中有“邑子呼延¨¨”,據姚薇元考證“呼延氏系出并州,即匈奴貴種呼衍氏之異譯”,姚薇元更指出北齊有呼延族。[]呼延族其人據《北齊書·高昂傳》:“(高昂)又隨高祖討尒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可知呼延族原是高昂的鄉人,與洛者村的呼延¨¨不僅同出匈奴貴種,亦皆在漢人的鄉村定居。只不過呼延族隨高昂建功擠身政權高層,而呼延¨¨仍待在村中成為佛教徒而已。東魏北齊確有周一良所說的“大鮮卑主義”,在軍隊裡表現尤其明顯,《通典·邊防》便云:“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詫曰:‘當銼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但不是所有鮮卑人皆屬兵戶,有些如賀蘭氏、鮮于氏、呼延氏久居鄉邑,與漢人協力造像,這便為“萬家燈火共華夷”的隋唐帝國打下基礎。五、北齊國策的轉向:“重武”變為“尚文” 但上述未能解釋北齊鮮卑若逐漸漢化,又怎會出現韓鳳這般仇恨漢人朝士的鮮卑人呢?韓鳳向來被視為鮮卑恩倖,但韓鳳之祖韓賢原屬尒朱陣營,在高歡起事後,轉歸其下。[]《北史·齊神武紀》說:“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高歡)同義,魏帝(孝武帝)忌之。”[]可知韓賢為勳貴,韓鳳自然是勳貴後裔,高歡又養韓鳳之姑為女,[]可知韓氏與高氏關係非同一般。此外,韓鳳會大受寵信,是被武成帝高湛選為後主高緯侍衛之故,[]這與他出身勳貴之後顯然關係甚大。同屬勳貴後裔的還有斛律光,斛律光是斛律金之子,斛律金在高歡欲反尒朱氏時“贊成大謀,仍從舉義。”高歡攻鄴,留斛律金守信都“委以後事”,[]因此斛律光與韓鳳皆出身勳貴勢力。《北史·韓鳳傳》又說:“(韓)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姐也,為此偏相參附”。[]段孝言是段榮之子、段韶之弟;而段榮是高歡的姐夫,高歡起兵時,段榮“贊成之”,往後高歡南征,也留段榮守信都,[]可見段榮亦是勳貴。段韶因“武明皇后(婁昭君)姐子,(高歡)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腹。”他除參與廣阿之戰外,並在決定高歡霸業的韓陵之戰中“督率所部,先鋒陷陣”,既為勳貴也是高澄、高洋的表兄弟,段韶之弟段孝言自然也屬勳貴勢力。韓鳳與斛律光、段孝言、段韶皆屬勳貴勢力;而受高歡遺命的正是此一勢力中人,[]可見在高歡心中,勳貴實為東魏政權的支柱,高氏兄弟唯有得勳貴助力,方能穩定他死後政局,並一統東西。[]高澄遵高歡遺言平侯景之反,甚或攻陷潁川、俘虜西魏王思政,[]但他未及討伐西魏即遇刺。其弟文宣帝高洋篡位後,並未忘卻高歡遺言,雖懍於高歡失敗前鑒從未主動出擊,[]仍欲誘使宇文泰舉兵東出。[]其弟孝昭帝高演登基後也要“雪神武(高歡)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高洋、高演既以消滅西魏為己任,勳貴在北齊的地位便屹立不搖,《北史·司馬膺之傳》所說:“班臺之貴,近世專以賞勳勤”,便是此一情況的描述。[]即使高演之弟高湛即位後“恣意作樂”,不復混一之志,[]卻仍重用勳貴段韶、斛律光以與北周抗衡。[]然而,在後主高緯親政後,勳貴的崇高地位卻開始動搖。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高湛崩於鄴宮乾壽堂,高緯開始親理國政。高緯將年號改為“武平”,並造“偃武修文臺”,明確宣示國策由“重武”轉為“尚文”。《北史·齊幼主紀》說高緯“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北齊書·文苑傳》亦稱高緯“頗好諷詠,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高緯還嫌杜臺卿所上之賦“未盡善”,要李德林重作。[]亦命文臣錄古代聖賢烈士與輕豔諸詩充圖畫,又“屬意斯文”,為編輯類書《修文殿御覽》廣招文士成立文林館,竟到“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的地步,亦可一窺高緯對文學的喜好之甚。[]北齊既“偃武修文”,軍務自不受重視。高緯將原本養馬的田賜給穆提婆,對後宮、恩倖又“一賜數萬匹”,卻吝於武備,以致“軍人皆無褌”。[]軍隊被輕視至此,恩倖便取代勳貴,在政壇炙手可熱。《北史·齊幼主紀》說高緯“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韓鳳)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然而《北史·齊幼主紀》卻漏載一位趁“偃武修文”之風崛起的恩倖,即祖珽。[]祖珽“詞藻遒逸,少馳令譽”又會說鮮卑語,但“不能廉慎守道”在魏齊政界載浮載沈。他雖在高湛居藩邸時刻意攀附,高湛即位後卻不敵和士開譖言被外放,是幫和士開出內禪策才“大被親寵”、“遂志於宰相”,又不敵和士開再被外放以致目盲。祖珽能重返中央,還是和士開、陸令萱“棄除舊怨”引為謀主之故。和士開死後,祖珽繼續黨附陸令萱,並在連續扳倒趙彥深、斛律光後,“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和士開系出鮮卑素和部,[]陸令萱則出自鮮卑步六孤氏,可知祖珽乃依附鮮卑恩倖才能登上高位。祖珽的政敵趙彥深則是勳貴司馬子如“賤客”出身,因司馬子如推薦得任高歡幕僚。趙彥深一度“以地寒被出”,也是司馬子如向高歡進言,才得任大丞相功曹參軍。[]司馬子如雖權傾一時,在高澄輔政後,聲勢卻大不如前,[]衣缽往後則被趙彥深承接,《北史·尉瑾傳》云:“武成(高湛)踐祚,趙彥深本(司馬)子如賓僚,……任遇彌重。”[]司馬子如“當時名士並加親愛”;趙彥深亦為時所重,“提獎人物,皆以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可知趙彥深雖屬勳貴勢力,卻與士人關係密切,這可能是欲執士人牛耳的祖珽屢次試圖將其扳倒的原因。祖珽藉陸令萱之力將趙彥深外放,又奏請設立文林館,更拜尚書左僕射“勢傾朝野”,這也讓斛律光對祖珽非常不滿,說:“盲人(祖珽)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更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祖珽便向高緯轉告不利斛律光的謠言,並說:“斛律累世大將,明月(斛律光)聲震關西,豐樂(斛律光之弟)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而從高緯往後所言:“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可知祖珽之言即暗指斛律光必反,當高緯詢問韓鳳意見時,韓鳳卻以“無此理”而“固執不從”,這是恩倖韓鳳對高緯罕有的頂撞,他與斛律光的關係顯然非同一般。高儼率軍入宮,事平,由斛律光、趙彥深處理其羽黨,兩人透過韓鳳將審問內情告知高緯,才“宣詔號令文武”。據《北史·高儼傳》,高儼案發後,高緯收高儼黨徒厙狄伏連等五人於後園,“親射之而後斬,皆肢解,暴之都街下。”對其餘“文武職吏盡欲殺之”,是斛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才“罪之各有差”,[]最終死者不過十餘人。[]可見斛律光、趙彥深為保全勳貴子弟,未多所牽連,居中協調的韓鳳雖無證據,但立場應與斛律光、趙彥深相同,否則以高緯雷霆之怒,勢必大肆株連,死者定然超過此數。還能從其他旁證,論證韓鳳立場屬勳貴勢力,《北史·穆提婆傳》說“自武平三年()之後,(陸)令萱母子勢傾內外,……令萱則自(胡)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穆)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唐邕時任尚書令,即內、外朝皆受陸令萱母子控制,大部分恩倖亦依附其下。《北史·齊幼主紀》說五位“宰制天下”的恩倖,扣除陸令萱、穆提婆,和士開、高那阿肱“皆為郡君(陸令萱)義子”。高阿那肱之父高市貴“從神武(高歡)以軍功封常山郡公”,[]可知高阿那肱乃勳貴之後,此時亦靠向陸令萱。三位“參預機權”的恩倖,陳德信曾向高緯告發穆提婆、韓鳳造宅事,[]應不附陸令萱,也不屬勳貴勢力。鄧長顒、何洪珍則與文林館關係匪淺。[]文林館是祖珽於武平三年()所奏立,而陸令萱母子自武平三年()之後“勢傾內外”,祖珽此時又委身其下,那文林館亦是陸令萱母子為迎合“頗好諷詠”、“屬意斯文”的高緯而設,因此鄧長顒、何洪珍也屬陸黨。陸黨“尚文”:陸令萱稱祖珽為“國師”、“國寶”。和士開“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穆提婆“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何洪珍則“有寵於後主(高緯),欲得通婚朝士。”鄧長顒更是勸高緯設文林館的關鍵人物。高阿那肱為勳貴之後,這時卻認陸令萱為義母,往後在北齊行將滅亡之際,高阿那肱與穆提婆皆投周軍;[]韓鳳卻仍“從後主(高緯)走渡河,到青州,並為周軍所獲。”因此,高阿那肱勳貴後裔的色彩已然淡化,應歸陸黨之林。高阿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還稱漢化的鮮卑人源師為“漢兒”,罵他“強知星宿”,似不能說陸黨盡“尚文”。然而比起“尤嫉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譖訴”的韓鳳,“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隱私,虛相讒構”的高阿那肱較為中道,不過仍存舊時鮮卑習氣而已。除上述所舉諸恩倖,還能從段孝言的動向來論證陸黨“尚文”。段孝言如前述乃屬勳貴勢力,也因此“致位通顯”,他卻協助祖珽拉下趙彥深,往後更入文林館待詔。祖珽失勢後,他又與有親戚關係的韓鳳“共構祖珽之短”。祖珽的得勢、失勢皆是陸令萱之故,可知段孝言也與高阿那肱一般依附陸令萱。段孝言其人“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可視為沾染文風的勳貴之後。比起大多“尚文”的陸黨,韓鳳卻“重武”:其人“有膂力,善騎射”、“帶刀走馬,未曾安行”、“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下容之”。又云:“恨不得剉漢狗飼馬!”更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對朝士則動致呵叱:“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所述與前述北齊前線部隊之言如出一轍。韓鳳“重武”又仇視文人,在恩倖中獨樹一格,將他視為殘存勳貴勢力之中堅,應無疑義。東魏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但到北齊末期,祖珽卻敢在高緯面前,對韓鳳說:“強弓長矟,容相推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祖珽與韓鳳論事時間不明,但待詔文林館的士人張雕虎也說:“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唐邕)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唐邕任尚書令是在武平三年()二月至武平五年()二月,張雕虎死於武平四年()十月,因此張雕虎必在武平三年()二月與武平四年()十月間批評唐邕。值得注意的是,斛律光死於武平三年()七月,即唐邕任尚書令五個月後,八月高緯便廢斛律光之女斛律后,改立胡太后侄女,十二月高緯再廢胡后,隔年二月改立陸令萱養女穆邪利為后。便意味陸令萱在短短四個月,接連擊敗斛律后與胡后背後的胡太后,[]這正是《北史·穆提婆傳》:“自武平三年()之後,(陸)令萱母子勢傾內外”的背景。祖珽也從斛律光之死獲得巨大政治利益,任領軍“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除開漢人任領軍的先例外,更讓高緯“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反觀,勳貴勢力連續遭逢趙彥深外放、斛律光被殺,實力大受損傷,韓鳳等人對隨陸黨聲勢高漲,“意氣甚高”的文士勢力,也只能“陰圖之”。張雕虎“以澄清為己任”,祖珽亦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朝廷,為致治之方”,甚欲拉穆提婆下馬,此時文士勢力之盛亦可見一斑。但祖珽不敵陸令萱而外貶,韓鳳把握良機,拒絕其面見後主之請,使之徹底失勢。[]趙彥深隨後重返中央,韓鳳則任領軍,但朝中文士勢力仍大,韓鳳遂一手炮製崔季舒之禍,其說動高緯的理由是:“漢兒文官聯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而祖珽置斛律光於死地的手段,正是“(斛律)光府參軍封士讓啟告光反”,韓鳳以文士諫止行幸晉陽為反,不過師法祖珽故智,報斛律光之死的一箭之仇而已。韓鳳雖藉文士勸阻高緯巡幸晉陽事,除去崔季舒、張雕虎等為首的五名文士,其餘聯名同署者,卻在趙彥深請求下,免受鞭撻之刑。[]韓鳳“常欲害之”的祖珽心腹顏之推,因未參與連署也得免禍。與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的李德林,在崔季舒事件後“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可見恩寵不衰。韓鳳雖剷除崔季舒等人,卻無力改變“偃武修文”的國策,文士勢力仍存留命脈,直至北齊滅亡。[]表面觀之,是得勢的陸黨“尚文”才使文士勢力崛起,若深層審視,陸令萱母子等人不過是迎合愛好詩文的高緯而已。高緯“尚文”,讓北齊國策轉為“偃武修文”,但大敵北周卻始終“重武”,這從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過程即可略窺端倪。北周明帝宇文毓被堂兄宇文護毒殺,臨終前命其大弟宇文邕繼位,[]但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的背後卻有一番波折,因其時攝政之宇文護也可立明帝之子宇文賢,卻因“天下事大”改立明帝之弟宇文邕。[]那“天下事”指涉為何呢?宇文泰臨終對宇文護云:“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北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可知“天下事”即是“諸子幼小,寇賊(北齊)未寧”,那麼宇文護以“天下事大”欲立長君,便是“重武”的表現。不僅高洋、高演兄弟為實現高歡遺言欲滅西魏、北周;宇文護、宇文邕兄弟亦想完成宇文泰遺願削平北齊。宇文護兩次聯合突厥東征,宇文邕親政後更戮力武備,“以海內未康,銳情敎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盧思道〈北周興亡論〉亦稱宇文邕“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啖。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反觀高緯則“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盛為無愁之曲,……自彈胡琵琶而唱之。”、“承武成(高湛)之奢麗,以為帝王當然。”[]即使如此,以北齊國力之強,北周要一舉統一華北仍非易事,李延壽論云:“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宇文邕)因機,遂混區夏。”[]“名將”、“忠臣”指的是斛律光。宇文邕聽聞斛律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入鄴後更說:“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顏之推亦言:“斛律明月(斛律光),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繫其生死。”[]可知斛律光之死乃北周混一北方的關鍵,而北齊國策轉為“偃武修文”,正是斛律光之死的背景,這也為北齊之亡埋下伏筆。六、鮮卑後裔的“文質化” 北齊國策轉向是因高緯“尚文”,但他不是鮮卑後裔中的特例,《北史·高淯傳》說:“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襄城王即高淯,高歡第八子。高淯無子,由其兄高演之子高亮嗣,高亮因周遭皆文藝之士,遂“美風儀,好文學。”[]廣寧王即高孝珩,高澄第二子。高澄雖“少壯氣猛,嚴刑峻法”,入鄴任吏部尚書後,“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遊宴,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高孝珩則“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璧自畫一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高澄長子,即高孝珩之兄高孝瑜“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高澄第四子高長恭,即引文所述之蘭陵王,雖以為將聞名,但史傳說他“貌柔心壯,音容兼美”[],應也與高澄的文化風尚有關。高洋“留心政術,以法御下”、“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並動輒殺人。[]但其嫡子廢帝高殷卻“貫綜經業”、“集諸儒講孝經”、“寬厚仁智”,對死囚“再三不斷其首”,使高洋“每言太子(高殷)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又說:“太子(高殷)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高演)。”[]高洋屬意接位的高演“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亦隨高洋討伐山胡,乃高洋諸弟中唯一有戰爭經驗者;[]即位後又曾在殿廷殺人,[]風格正似高洋,但高演仍重《經》學,登基後即下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高澄)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與高演不同,高湛即位後轉而推崇文學,河清二()正月,他首開先例,“臨朝堂策試秀才”。[]當時選拔秀才考的是“緝綴辭藻”,[]那麼高湛親自策試秀才,其實也與高緯一般“屬意斯文”。不僅高氏,連勳貴後裔也出現“文質化”跡象。段孝言父兄都為勳貴,他卻重視士人、推崇文藝已見前述。韓軌隨高歡舉兵,自屬勳貴,其子韓晉明“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司馬子如之侄司馬膺之則“有風貌,好學,……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邢邵)、王元景(王昕)等並為莫逆之交。”、“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揚雄)周旋。’”[]高歡是高氏子孫“文質化”的奠基者,《北齊書·儒林傳》載: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高歡)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高洋)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虎)、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盧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又好釋氏,通其大義”,[]乃兼儒釋道三家的大儒。繼盧景裕為高歡諸子師的李同軌,亦“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可知高歡延請教授子弟的皆屬當世通儒。然而高洋對學習興趣不大,《北史·齊文宣紀》說他:“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他卻看重其子教育,即位後禮聘李寶鼎、邢峙為高殷講學。前述劉晝與李寶鼎為同鄉,李寶鼎“授其三《禮》”。[]北齊末大儒熊安生因“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可見李寶鼎擅長三《禮》,邢峙亦通三《禮》,在此環境薰陶下,高殷重《禮》也就不足為奇了,天保七年(),高洋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高殷“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可見其《禮》學造詣有相當水準。高演“留心政術”卻重《經》學,也與高歡佈置的教育環境有關。《北史·齊孝昭紀》說高演“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高演“不好辭彩”,其弟高湛卻“好辭彩”,除特意親臨朝堂策試秀才外,更因李德林所作辭頌優美而賜名馬一匹。[]其實高湛之兄高澄、高洋亦好文學,這從“一國大才”魏收的宦海浮沈便可瞭解。魏收系出鉅鹿魏氏,是當時著名的文人,孫搴死後,司馬子如推薦他到晉陽擔任中外府主簿,卻不受高歡賞識,“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棰楚,久不得志。”即使司馬子如向高歡當面陳說,高歡仍“未甚優禮”,魏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然而,魏收“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之句,卻被高澄大讚:“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彩。”往後亦因作〈詔〉,被高洋“大嗟賞”。高洋更一度欲讓魏收任中書監,可見對其器重異常。但在“不好辭彩”的高演即位後,魏收便被冷落,文史之任皆被剝奪;直到高湛登基,以魏收“才名振俗”對其“虛心倚仗”,他才又重回政治核心。高澄兄弟對魏收之文極為欣賞,而魏收行文卻模仿南朝任昉之風格。[]唐長孺認為這反映北齊士人對南朝文學的崇仰,[]那也可說,高澄兄弟讚賞魏收之文,即是對南朝文學的仰慕,亦是“文質化”的表徵。[]高澄兄弟愛好文學也與高歡有關。東西魏一分立,高歡即遷都於鄴,“戶四十萬狼狽就道”,[]高歡同時也將洛陽的頂尖文士遷移至鄴,《北齊書·文苑傳》載:有齊自霸業雲啟,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邢邵)、鉅鹿魏伯起(魏收)、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祖珽)、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陽休之)並其流也。[]鄴都濃郁的文化氛圍正是高氏、勳貴等鮮卑後裔逐漸“尚文”的大背景,也是文士勢力根基之所在。高氏子孫、勳貴後裔久居鄴都者,受此氛圍影響逐步“文質化”,但因高歡重視子弟教育,高氏子孫“文質化”程度又高於勳貴後裔。即使如此,高澄、高洋、高演為實現高歡遺言,文武之間更“重武”;高湛雖不復進取、喜好文學,為對抗北周仍繼續重用勳貴,此一國策卻在高緯親政後徹底瓦解。值得注意的是,高緯在高湛死後順利保住皇位,為高氏第三代首次成功接班,也是高湛鑒於高殷繼位失敗,苦心鋪陳的結果。高殷、高緯兩人不僅同屬第三代,兩人也異常相似:同樣高度“文質化”(高殷尚《禮》學,高緯好文學)、同樣“性懦”、同樣為此差點被廢。[]高洋在歷經一番掙扎後仍傳位高殷,高演卻發動政變奪取大位,死前更令高湛承統,讓第二代依然控制朝局。高湛為確保君位能父死子繼,於生前內禪於第三代高緯,高緯在親政後卻將父兄輩已有的“尚文”傾向推展至極;而北周卻仍是不忘先輩遺志的第二代宇文邕在位,故能維持“重武”精神於不墜,最終便導致北齊的滅亡。[]七、結論 學界大多以“大鮮卑主義”或“鮮卑化”來把握東魏北齊的文化特質,本文認為東魏北齊鮮卑已逐漸漢化,表現在漢語成為朝廷的通用語、鮮卑以漢名為正式名、基層胡漢混居,以及國策轉變、鮮卑後裔的“文質化”等幾個面相,可知漢文化對鮮卑的影響顯然不低,國策轉為“偃武修文”,甚至是北齊滅亡的原因之一。即使如此,並不能以此認定鮮卑與漢人已全然混融,在少數的鮮卑如韓鳳心中仍有極強的胡漢分野,但卻能肯定大多數鮮卑朝漢化方向邁進。如果東魏北齊政治衝突中胡漢文化差異並非主要,那是否還存在其他的根本動因,是值得再深究的問題。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專書: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陳文和編:《嘉定王鳴盛全集(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年。 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 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年影印本。 李昉:《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年影印本。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年。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 周一良:《周一良集: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年。 吳先寧:《北朝文化特質與文學進程》。北京:東方出版社,年。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華書局,年。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北京:中華書局,年。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年。 曹道衡:《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年。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稿》。北京:三聯書店,年。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年。 陳寅恪口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社,年。 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年。 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史通》。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年點校本。 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 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年影印本。 韓理洲編:《全北齊北周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年。 韓理洲編:《全北魏東魏西魏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年。 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 (二)論文: 仇鹿鳴:〈“攀附先世”與“偽冒士籍”-以渤海高氏為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第2期(年4月),頁60-74。 江中柱:〈高歡、高澄父子與東魏的漢化〉,《福州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年4月),頁73-76。 李紅豔:〈關於北齊北周反漢化問題的認識〉,《大同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3期(年9月),頁16-26。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北齊政治史與漢人貴族〉,載《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 呂一飛:〈論北朝鮮卑文化的歷史作用〉,《文獻》,第1期(年4月),頁-。 何德章:〈北朝鮮卑族人名的漢化─讀北朝碑誌劄記之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4輯(年6月),頁39-47。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政策與民族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年,頁-。 周一良:〈論宇文周之種族〉,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年,頁-。 周一良:〈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年,頁-。 胡勝源:〈“武風壯盛”到“重文輕武”—再論北齊傾覆之因〉,《興大歷史學報》,第20期(年8月),頁1-16。 范兆飛:〈中古地域集團學說的運用及流變〉,《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第1期(年2月),頁13-25。 唐長孺:〈拓跋族的漢化過程〉,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中華書局,年,頁-。 孫同勛:〈北魏末年與北齊時代的胡漢衝突〉,《思與言》,第4期(4年11月),頁-。 徐中原:〈東魏北齊漢化及其文教建設-兼和陳寅恪先生請教商榷〉,《現代語文》,第6期(年6月),頁14-16。 徐璇:〈論北齊的胡化漢化問題─以北齊高氏家族為中心〉,《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5期(年10月),頁84-89。 陳寅恪:〈《北朝胡姓考》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年,頁-。 許福謙:〈東魏北齊胡漢之爭新說〉,《文史哲》,第3期(年6月),頁26-29。 張國安:〈試論六鎮鮮卑的民族融合〉,《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年2月),頁27-32。 張金龍:〈高歡家世族屬真偽考辨〉,載《考古論史-張金龍學術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年,頁-。 黃永年:〈論北齊的文化〉,載《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年,頁21-31。 黃壽成:〈以高歡家族為例看東魏北齊漢化〉,《暨南史學》,第六輯(年12月),頁-。 黃壽成:〈北朝後期高歡家族與宇文泰家族漢化之比較〉,《許昌學院學報》,第6期(年12月),頁38-46。 漆澤邦:〈論東魏-北齊的倒退〉,載《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年6月),頁-。 蕭璠:〈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食貨月刊》,第8期(年11月),頁-。 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3分(年7月),頁-。 錢龍、馬軍:〈東魏北齊的漢化形勢〉,《滄桑》,第5期(年5月),頁19-20。 繆鉞:〈北朝的鮮卑語〉,載《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年,頁53-77。 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載《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年,頁78-94。 聶鴻音:〈鮮卑語言解讀述論〉,《民族研究》,第1期(年2月),頁63-70。 羅新:〈說《文館詞林》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中國史研究》,第1期(年2月),頁。 羅新:〈北齊韓長鸞之家世〉,《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第1期(年2月),頁-。 蘇航:〈“漢兒”歧視與“胡姓”賜與:論北朝的權利邊界與族類邊界〉,《民族研究》,第1期(年2月),頁92-。 二、日文: (一)論文: 濱口重國:〈高齊出自考—高歡の制霸と河北の豪族高乾兄弟の活躍〉,載《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6年,頁-。 橫山裕男:〈北齊の恩倖について〉,載《中國中世史研究續編》,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年,頁-。 山崎宏:〈北周の麟趾殿と北齊の文林館〉,載《鈴木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叢》,東京:明德出版社,年,頁-。 注釋: [1]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年),頁48:“東西兩國俱以六鎮流民創業,初自表面觀察,可謂魏孝文遷都洛陽以後之漢化政策遭一大打擊,而逆轉為胡化,誠北朝政治社會之一大變也。”、陳寅恪口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社,年),頁-:“北齊的民族成見很深,這種民族成見以‘化’分,非以血統分。其表現為佔據統治地位的鮮卑化人,反對、排斥與殺害漢化與漢化之人。北齊之所以為出現這樣一種反常情況,是因為北齊的建立,依靠六鎮軍人。而六鎮軍人作為一個保持鮮卑化的武裝集團,本是洛陽漢化文官集團的反對者。六鎮起兵是對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反動。這種反動,在北齊的鮮卑化中表現出來了。” [2]唐長孺:〈拓跋族的漢化過程〉,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中華書局,年),頁-、繆鉞:〈北朝的鮮卑語〉,載《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年),頁78-93、漆澤邦:〈論東魏-北齊的倒退〉,載《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成都,年),頁-、呂一飛:〈論北朝鮮卑文化的歷史作用〉,《文獻》,年第1期,頁。唐長孺雖討論了六鎮起兵後內遷鮮卑與“鮮卑化”人民的漢化,並名之以“拓跋族的第二次漢化”。卻云:“(東魏北齊)統治者把鮮卑或鮮卑化的人民和漢族人民隔離開的企圖是違反當時各族融合的總傾向的,對於漢族和鮮卑人民都沒有好處,因而其結果便招致了北齊王朝自身的滅亡。滅亡以後的北齊境內鮮卑或鮮卑化人民或者改編到北周的府兵系統中,或者散處民間,而兩者同樣地最後和漢族融合。”可知,唐長孺說的“拓跋族的第二次漢化”,是在東魏北齊因胡漢隔閡而滅亡的基礎上完成的。 [3]繆鉞:〈北朝的鮮卑語〉,頁65。 [4]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年),頁。 [5]周一良:〈北朝的民族政策與民族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年),頁-。 [6]張國安:〈試論六鎮鮮卑的民族融合〉,《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年第1期,頁27-32。 [7]黃永年:〈論北齊的文化〉,載《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年),頁21-31。 [8]何德章:〈北朝鮮卑族人名的漢化─讀北朝碑誌劄記之一─〉,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武漢:武漢大學學報編編輯部,年),第14輯,頁44-45。伴隨人名漢化的是鮮卑對漢人郡望的冒附,橫山裕男、羅新皆指出,系出勳貴之後的韓鳳(韓長鸞),一邊極端厭惡漢人,一邊卻又冒附昌黎韓氏譜系。羅新對此有一針見血的解釋:“學界關於北齊統治集團‘胡化’傾向研究,關於六鎮勳貴‘反漢化’的討論,當然是有根據的,能夠得到史料的支持。但是我們也知道歷史運動是複雜的、多方向的,單一時期、單一側面的觀察,不足以得出全面的結論,也不足以概括歷史運動的實際,從上面看有關部分六鎮勳貴攀附華夏郡望的討論來看,北齊統治者多多少少接受了華夏傳統的影響,並多多少少地向著這種傳統低頭。無論是居於統治集團最頂端的高氏,還是普通勳貴的韓氏,都以改造家族譜系的行為,實際上表達向華夏認同態度。這意味著,無論北齊統治集團多麼不情願放棄他們的六鎮傳統,但進入中原之後,接受華夏傳統的影響,逐漸改造自己的文化面貌,就成為不可迴避的歷史方向。”請參橫山裕男:〈北齊の恩倖について〉,載《中國中世史研究續編》(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年),頁-、羅新:〈北齊韓長鸞之家世〉,《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年第1期,頁-。此外,“勳貴”,依谷川道雄的定義乃“高歡在懷朔鎮、信都舉兵以及平定尒朱氏後的各個階段中,為他掌握霸權而盡力的一群人。”請參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北齊政治史與漢人貴族〉,載《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 [9]唐長孺:〈拓跋族的漢化過程〉,頁。 [10]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北京:中華書局,年),頁52-68。 [11]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年第63本第3分,頁。 [12]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載《讀史存稿》,頁78-94、孫同勛:〈北魏末年與北齊時代的胡漢衝突〉,《思與言》,4年第4期,頁-、蕭璠:〈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食貨月刊》,年第8期,頁-、許福謙:〈東魏北齊胡漢之爭新說〉,《文史哲》,年第3期,頁26-29、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年),頁-、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年),頁-。其中對當代學界影響最鉅的典範性研究是呂春盛與王怡辰的作品,因其論證主軸與本文關係較淺,擬於他文深入闡述。 [13]黃永年:〈論北齊的政治鬥爭〉,載《文史探微》,頁55-61。 [14]胡勝源:〈“武風壯盛”到“重文輕武”─再論北齊傾覆之因〉,《興大歷史學報》,年第20期,頁1-16。 [15]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稿》,頁48。 [16]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稿》,頁49。 [17]李紅豔:〈關於北齊北周反漢化問題的認識〉,《大同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年第3期,頁16-26、江中柱:〈高歡、高澄父子與東魏的漢化〉,《福州大學學報(哲社版)》,年第2期,頁73-76、錢龍、馬軍:〈東魏北齊的漢化形勢〉,《滄桑》,年第5期,頁19-20、黃壽成:〈以高歡家族為例看東魏北齊漢化〉,《暨南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年),第六輯,頁-、徐中原:〈東魏北齊漢化及其文教建設─兼和陳寅恪先生請教商榷〉,《現代語文》,年第6期,頁14-16、黃壽成:〈北朝後期高歡家族與宇文泰家族漢化之比較〉,《許昌學院學報》,年第6期,頁38-46、徐璇:〈論北齊的胡化漢化問題─以北齊高氏家族為中心〉,《天水師範學院學報》,年第5期,頁84-89。 [18]胡勝源:〈“武風壯盛”到“重文輕武”─再論北齊傾覆之因〉,頁7-12。 [19]周一良:〈北朝的民族政策與民族問題〉,頁-。 [20]唐長孺:〈拓跋族的漢化過程〉,頁-。 [21]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卷55,〈孫搴傳〉,頁-。 [22]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卷中,〈地形志〉,頁2-3。 [23]魏收:《魏書》,卷11,〈前廢帝紀〉,頁。 [24]李延壽:《北史》,卷47,〈祖珽傳〉,頁6-8。 [25]李延壽:《北史》,卷24,〈王昕傳〉,頁。 [26]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卷31,〈王昕傳〉,頁、李百藥:《北齊書》,卷30,〈崔昂傳〉,頁。 [27]李延壽:《北史》,卷33,〈李繪傳〉,頁7。 [28]李百藥:《北齊書》,卷29,〈李繪傳〉,頁、。 [29]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昂傳〉,頁。 [30]張國安:〈試論六鎮鮮卑的民族融合〉,頁30。 [31]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 [32]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頁78-82。 [33]陳寅恪口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 [34]濱口重國:〈高齊出自考—高歡の制霸と河北の豪族高乾兄弟の活躍〉,載《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6年),頁-。仇鹿鳴以渤海高氏與鄉里社會關係密切,高歡所出的高謐一支卻可能來自胡人聚集的河州,認為濱口說符合事實。請參仇鹿鳴:〈“攀附先世”與“偽冒士籍”—以渤海高氏為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年第2期,頁71-72。 [35]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頁82。 [36]周一良:〈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頁-。 [37]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華書局,年),頁-。 [38]譚其驤之論出自與繆鉞書信,但遍尋譚氏文集,未見此信,唯存繆鉞之文附錄,請參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頁93-94。 [39]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21-25。 [40]張金龍:〈高歡家世族屬真偽考辨〉,《考古論史-張金龍學術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年),頁-。 [41]陳寅恪口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 [42]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昂傳〉,頁。 [43]李延壽:《北史》,卷31,〈高昂傳〉,頁7。 [44]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 [45]李百藥:《北齊書》,卷19,〈劉貴傳〉,頁。 [46]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年影印本),頁9-1。 [47]李百藥:《北齊書》,卷24,〈杜弼傳〉,頁:“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為‘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 [48]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點校本),卷18,〈雜說下第九〉,頁。 [49]李延壽:《北史》,卷28,〈源師傳〉,頁2-3。 [50]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卷,“陳宣帝太建五年()”,頁。 [51]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卷1,〈文帝紀上〉,頁1。 [52]周一良:〈論宇文周之種族〉,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頁-。 [53]蘇航:〈“漢兒”歧視與“胡姓”賜與:論北朝的權利邊界與族類邊界〉,《民族研究》,年第1期,頁94、98。 [54]周一良:〈論宇文周之種族〉,頁。 [55]令狐德棻:《周書》,卷11,〈宇文護傳〉,頁。 [56]黃壽成從高歡包容儒士一事,論證其漢化程度勝於宇文泰,卻未比較兩者漢語能力的優劣,本文所論便能完善其說。請參黃壽成:〈北朝後期高歡家族與宇文泰家族漢化之比較〉,頁45。 [57]令狐德棻:《周書》,卷26,〈長孫儉傳〉,頁-。 [58]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史通》,卷18,〈雜說下第九〉,頁-。 [59]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史通》,卷17,〈雜說中第八〉,頁。 [60]魏徵:《隋書》,卷42,〈李德林傳〉,頁8。 [61]唐長孺:〈拓跋族的漢化過程〉,頁-。 [62]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卷32,〈經籍志〉,頁。 [63]周一良:〈北朝的民族政策與民族問題〉,頁-。 [64]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卷1,〈教子篇〉,頁21。 [65]韓鳳是北齊末極端仇視漢人官員的鮮卑顯宦,但史籍僅此一例,孤證無法成證,便難以據此認定鮮卑官員皆如韓鳳一般視漢人如仇寇。 [66]陳寅恪:〈《北朝胡姓考》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年),頁。 [67]李百藥:《北齊書》,卷42,〈陽休之傳〉,頁-。 [68]李延壽:《北史》,卷53,〈斛律金傳〉,頁5-6。 [69]聶鴻音:〈鮮卑語言解讀述論〉,《民族研究》,年第1期,頁70。 [70]李延壽:《北史》,卷53,〈万俟普傳〉,頁0。 [71]李延壽:《北史》,卷53,〈万俟受洛干傳〉,頁0。 [72]李延壽:《北史》,卷53,〈可朱渾元傳〉,頁0。 [73]李延壽:《北史》,卷53,〈厙狄盛傳〉,頁8。 [74]李百藥:《北齊書》,卷17,〈斛律金傳〉,頁。 [75]李延壽:《北史》,卷53,〈万俟普傳〉,頁0。 [76]周一良:〈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頁。 [77]李百藥:《北齊書》,卷27,〈可朱渾元傳〉,頁。 [78]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陳文和編:《嘉定王鳴盛全集(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頁。 [79]李延壽:《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 [80]李延壽:《北史》,卷6,〈齊文襄紀〉,頁。 [81]李延壽:《北史》,卷7,〈齊文宣紀〉,頁。 [82]李延壽:《北史》,卷7,〈齊孝昭紀〉,頁。 [83]李延壽:《北史》,卷8,〈齊武成紀〉,頁。 [84]李延壽:《北史》,卷51,〈齊宗室諸王傳〉,頁9-8。有*標示者因史料缺載以〈高洧墓誌〉、〈高湜墓誌〉補,趙超編:《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年),頁。 [85]李延壽:《北史》,卷55,〈陳元康傳〉,頁、李百藥:《北齊書》,卷15,〈尉景傳〉,頁-。 [86]張國安:〈試論六鎮鮮卑的民族融合〉,頁30。 [87]李延壽:《北史》,卷51,〈高浚傳〉,頁1。 [88]李百藥:《北齊書》,卷17,〈斛律光傳〉,頁、。 [89]史書中並未記載韓賢之子的姓名,橫山裕男據《韓裔墓誌》考證出墓主韓裔之父的履歷與韓賢最為相似,似乎是同一人。橫山氏的說法可信,韓賢的兒子是韓裔(字永興),他的孫子即是北齊末著名恩倖韓鳳(字長鸞)。參橫山裕男:〈北齊の恩倖について〉,頁-。 [90]李延壽:《北史》,卷7,〈齊廢帝紀〉,頁。 [91]李延壽:《北史》,卷51,〈齊宗室諸王傳〉,頁5-3。 [92]魏收:《魏書》,卷74,〈尒朱榮傳〉,頁0。 [93]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 [94]令狐德棻:《周書》,卷11,〈宇文護傳〉,頁。 [95]令狐德棻:《周書》,卷20,〈賀蘭祥傳〉,頁。 [96]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頁-。 [97]李百藥:《北齊書》,卷24,〈孫搴傳〉,頁-。 [98]魏收:《魏書》,卷,〈地形志〉,頁-3。 [99]〈邑義五百人造像記〉,韓理洲編:《全北魏東魏西魏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年),頁-。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頁32-37。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頁-。 []魏收:《魏書》,卷,〈地形志〉,頁。 []〈僧通等八十人造像記〉,韓理洲編:《全北齊北周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年),頁-。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頁-。 []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昂傳〉,頁。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年點校本),卷,〈邊防〉,頁。 []李延壽:《北史》,卷53,〈韓賢傳〉,頁5。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 []李延壽:《北史》,卷41,〈燕子獻傳〉,頁7。 []李延壽:《北史》,卷92,〈韓鳳傳〉,頁。 []李百藥:《北齊書》,卷30,〈斛律金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92,〈韓鳳傳〉,頁。 []李百藥:《北齊書》,卷16,〈段榮傳〉,頁。 []李百藥:《北齊書》,卷16,〈段韶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55,〈陳元康傳〉,頁載高歡對高澄遺言:“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 []李延壽:《北史》,卷55,〈陳元康傳〉,頁-。 []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年影印本),卷,〈兵部〉引《三國典略》,頁6之1。 []李百藥:《北齊書》,卷4,〈文宣紀〉,頁59。 []李百藥:《北齊書》,卷6,〈孝昭紀〉,頁85。 []李延壽:《北史》,卷54,〈司馬膺之傳〉,頁0。 []李延壽:《北史》,卷92,〈和士開傳〉,頁。 []胡勝源:〈“武風壯盛”到“重文輕武”─再論北齊傾覆之因〉,頁4-6。 []李延壽:《北史》,卷8,〈齊幼主紀〉,頁-。 []魏徵:《隋書》,卷42,〈李德林傳〉,頁7。 []李百藥:《北齊書》,卷45,〈文苑傳〉,頁-。 []李百藥:《北齊書》,卷30,〈斛律光傳〉,頁。 []祖珽多重黨派身分的研究,請參范兆飛:〈中古地域集團學說的運用及流變〉,《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年第1期,頁20-21。 []李延壽:《北史》,卷47,〈祖珽傳〉,頁6-2。 []《北史·和士開傳》說和士開出身西域商胡(李延壽:《北史》,卷92,〈和士開傳〉,頁頁),羅新據魏收撰《征南將軍和安碑銘》考證出和士開乃代北素和部出身,詳細討論請參羅新:〈說《文館詞林》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中國史研究》,年第1期,頁。 []李延壽:《北史》,卷55,〈趙彥深傳〉,頁。 []李百藥:《北齊書》,卷18,〈司馬子如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20,〈尉瑾傳〉,頁。 []李百藥:《北齊書》,卷30,〈斛律光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52,〈高儼傳〉,頁1。 []李延壽:《北史》,卷92,〈和士開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92,〈穆提婆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92,〈高阿那肱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92,〈韓鳳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81,〈張景仁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44,〈崔劼傳〉,頁4。 []李延壽:《北史》,卷92,〈穆提婆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92,〈高阿那肱傳〉,頁。 []李百藥:《北齊書》,卷16,〈段孝言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92,〈韓鳳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81,〈張雕武(虎)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8,〈齊後主紀〉,頁-。 []李延壽:《北史》,卷47,〈祖珽傳〉,頁3。 []李百藥:《北齊書》,卷39,〈崔季舒傳〉,頁-。 []魏徵:《隋書》,卷42,〈李德林傳〉,頁7-8。 []胡勝源:〈“武風壯盛”到“重文輕武”─再論北齊傾覆之因〉,頁13。繆鉞指出東魏北齊有三次胡漢政治衝突,但據呂春盛研究應為兩次:其一是乾明之變,其二則為崔季舒事件。呂氏在分析乾明之變時指出:“這次政變雖是胡漢兩集團的衝突,但衝突卻是緣著權力的轉移而爆發的,從這一觀點來看,可以說胡漢衝突的背後同時潛在著權力轉移的問題。”(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也就是說此次衝突族群紛爭只是表象,根本乃權力之爭。至於崔季舒事件,由前述分析可知,乃北齊由“重武”轉向“修文”,文人隨之掌權的結果,亦屬權力爭奪,則繆鉞說便有修正的必要。 []令狐德棻:《周書》,卷4,〈明帝紀〉,頁59。 []令狐德棻:《周書》,卷35,〈崔猷傳〉,頁。 []令狐德棻:《周書》,卷11,〈宇文護傳〉,頁。 []令狐德棻:《周書》,卷6,〈武帝紀下〉,頁。 []李昉:《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年),卷,〈北周興亡論〉,頁0。限於篇幅,北周“重武”面相只能簡略陳述,將於另文詳細探討。 []李延壽:《北史》,卷8,〈齊幼主紀〉,頁。 []令狐德棻:《周書》,卷6,〈武帝紀下〉,頁。 []李百藥:《北齊書》,卷30,〈斛律光傳〉,頁。 []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卷2,〈慕賢篇〉,頁。 []李延壽:《北史》,卷51,〈高淯傳〉,頁5。 []李延壽:《北史》,卷6,〈齊文襄紀〉,頁。 []李延壽:《北史》,卷52,〈高孝珩傳〉,頁6。 []李延壽:《北史》,卷52,〈高孝瑜傳〉,頁5。 []李延壽:《北史》,卷52,〈高常恭傳〉,頁0。 []李百藥:《北齊書》,卷4,〈文宣紀〉,頁67-68。 []李延壽:《北史》,卷7,〈齊廢帝紀〉,頁-、。 []李延壽:《北史》,卷56,〈魏收傳〉,頁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梁元帝承聖三年()”,頁5。 []李延壽:《北史》,卷24,〈王晞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7,〈齊孝昭紀〉,頁、。 []李百藥:《北齊書》,卷7,〈武成紀〉,頁91。 []李百藥:《北齊書》,卷44,〈劉晝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54,〈韓軌傳〉,頁8-9。 []李延壽:《北史》,卷54,〈司馬膺之傳〉,頁0-1。 []李百藥:《北齊書》,卷44,〈儒林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30,〈盧景裕傳〉,頁9。 []李延壽:《北史》,卷33,〈李同軌傳〉,頁0。 []李延壽:《北史》,卷7,〈齊孝昭紀〉,頁。 []李延壽:《北史》,卷81,〈劉晝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82,〈熊安生傳〉,頁4。 []李延壽:《北史》,卷7,〈齊孝昭紀〉,頁。 []李延壽:《北史》,卷42,〈李德林傳〉,頁7。 []李延壽:《北史》,卷56,〈魏收傳〉,頁7-4。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年),頁。 []山崎宏考察文林館文士,發現南朝士人流寓者比例甚高,將之視為北齊文藝界崇拜南朝文化的表徵。吳先寧、曹道衡也都指出東魏北齊文學深受南朝影響,請參山崎宏:〈北周の麟趾殿と北齊の文林館〉,載《鈴木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叢》(東京:明德出版社,年),頁、、吳先寧:《北朝文化特質與文學進程》(北京:東方出版社,年),頁57、曹道衡:《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年),頁。 []李延壽:《北史》,卷6,〈齊神武紀〉,頁。 []李百藥:《北齊書》,卷45,〈文苑傳〉,頁-。 []李延壽:《北史》,卷52,〈高儼傳〉,頁9:“(高儼)又言於帝(高湛)曰:‘阿兄(高緯)懦,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高緯)為劣,有廢立之意。” []關於北齊衰亡的原因,前輩學者由外而內,分析已極為詳盡、深入。本文不過是在前人基礎上,強調“文質化”對北齊滅亡所產生的作用,並非以為此乃唯一因素。此外,高緯雖“偃武修文”,卻不能視之為漢人。因其崇尚《禮》學的堂兄高殷,卻稱:“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李延壽:《北史》,卷41,〈楊愔傳〉,頁6)可知,仍自視為鮮卑。再者,高緯“尚文”雖是東魏北齊政治傳統改變的轉捩點,此舉卻是在前代高澄、高洋、高演、高湛“文質化”的基礎上深化,非僅個人興趣的展現。最後,東魏北齊鮮卑漢化程度所以超過西魏北周,除洛陽-鄴的文化基盤外,還有山東富強資源為憑藉,西魏才要特意推行“關中本位政策”以“胡(鮮卑)化”團結胡漢對抗大敵,這也是北周能沿續“尚武”精神的另一個原因。關於北齊衰亡諸因素的討論,請參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51-。 本文刊於《人文中國學報》第32期,1年5月,第47~81頁。如有引用,請查閲原文。感謝胡勝源先生授權發佈。編輯:劉藝穎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erfenga.com/nefyfyl/8443.html
- 上一篇文章: 冠源知否原来成语不全是四个字,这些三字成
- 下一篇文章: 笑谭间气吐霓虹海上篆刻名家陆康小记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