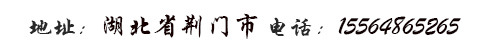凹河意象
|
就地名而言,凹河这个名字,直白、通俗。即便是没到过的人,一听,自然而然,脑子里就有了轮廓,有了形象。但也仅局限于此——在坡多坎多,沟多汊多的贵州山乡,类似地名,实在太多。所以,若不是亲身趟过,仅凭一个名字,在大家心里,实在是翻不起那么一丁点浪花。 因此,凹河是低调的。低调的凹河,就如《见与不见》: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山,还是那样,两岸高耸,不言不语;水,还是那样,不疾不徐,淙淙流淌。它们,经历了什么,见证了什么,包容了什么,我们实在无法知道太多。这种感觉,让人无可奈何,甚至抓狂。怎么形容呢,如一指流沙?一场雾罩?对了,凹河人确切是把半天云中那一团团的雾,称着罩子的。罩着的,就是迷离,还有未知。 我不知道这样的折腾,有着怎样的意义。或许,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像弟子小桥发,一直在我耳边嘤嘤,说:凹河的弯道,有九道。凭直觉,我不认为会有这么多。于是就试着去数,数来数去,还是没凑上这个数。但小桥发就不这样认为,而且,对于其他人不同的结果,他就急,那态度,不容一点质疑。我不善于争辩,正打算搁置,他却直来直去,把问题交给了桥边摆摊子的老人。结果,老人一个白眼:幺,有力气,过几天记倒回来,你家坡上的樱桃,快要熟了。 这句话,仿佛一炸雷,在我耳边轰轰着响。我仿佛明白,我不该倔着一股劲,去解构一座山,一条河。在它们面前,我们就是蝼蚁。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姿势,去走进它们?我想,至少要心怀两个词:感恩、仰望;而后,试着与它们心气相同,血脉相连,直至融为一体,让自己心里,也流着一条河,住着一座山。 这个想法灵光一闪,耳朵里面,就有了一个声音,粗犷而辽远:哦——吼!哦——吼!那是一个精壮的汉子,麻衣、麻裤,腰上,拴着一根藤,别着一把亮晃晃的弯刀。他的身后,还有一群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个个的眼里,也随着这一声“哦——吼”,闪动着激动的光。 他们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但从他们瘦削的身躯、褴褛的衣衫上看,他们一定走了许多路,吃了许多苦。一路跋涉,一路风餐,直至——看到凹河那两扇高高的门,那蜿蜒流淌的河。他们停下了脚步。他们想,这应该就是家了。你看,沿河两岸,土地多肥;牛儿喝了这清清的水,还不一个劲地长?于是,他们假茅为瓦,筑土成墙。男人开荒辟草,女子织衣带娃。他们认为,这就是日子该有的模样,吼一声,山映水映,叹一句,地久天长。 一日一日,一年一年,他们的气息,融进了这片山水。那高耸的大山,是他们栖息的臂弯;那一弯河流,就是他们连接母体的脐带。山无言,水无言,他们就试着,用一种亲切的、朴素的,有着大山原色的语言,来为它们命名:抬头见山,低头是河,不就是凹河?哪怕,在这错落的山坳,生活的子民,已练就一身好手,如猿似猱,如鹰如燕,但从山垴垴过来,还得心有敬畏,紧紧怀抱那方凸起,那就是“抱腰岩”了。对了,大石板下面的河湾,远看,挤挤挨挨,仿若一体,即便是家里的大黄狗,仿佛一纵步,就可以过去。纵是如此,还得有座桥吧?于是,坎坎伐檀,藤树相缠,姑且,就唤着狗桥吧,听起来,亲切。别说,往上一过,晃晃悠悠,就如晚归时刻,踩上河滩的软绵。 天亮了,出工了,天黑了,吃饭了。张家嫁姑娘,陪嫁的家具,堆了一屋子;李家生了娃,足足八斤,不显山不露水的李老伯,毫不犹豫就宰了一头猪,从村头,一直请到村尾。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奈何有一天,或许是一个漆黑的夜,一阵杂乱的脚步,突然惊扰了大家的梦。守家的狗儿,突然噤声;含着奶头的娃,睁大了惊恐的眼,老半天,不见眨一眨。女子无助的哭泣,男人的愤怒和无奈,换回的,只是漠然,只是兵戈的冷,还有经久不息的火药的弥漫。 这片土地,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战祸?故纸堆里,实在拎不出相关记载。小桥发说,听桥边老人讲,河对岸高高的屯上,却曾留下了许多遗迹。不过山高坡陡,难得一见。但河这一侧,大山半崖上,我却不止一次,抚摸过那扇厚厚的石门。这是怎样的工事哦,回头,不是岸,是仅容一人行走的茅狗路;脚下,是千仞悬崖,透过横斜的枝叶,只见一荡一荡的绿波,晃得人直打颤。石门筑于何时,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没人知道,但它无疑,就是山民避祸之所。仅容三四人并排的岩壁上,凿有猪槽、碓窝,不远处,还有一口赖以生存的井。想来,住在悬崖的日子,绝非三月两月。兵者,凶器也!其凶何如?凹河之一隅,老院高坡上,不时,还可见一口口出土的石棺。让人无法不去想象,这片土地,曾发生了如何激烈的战事。 对这些过往,老人们往往讳莫如深。就如小桥发,不愿去那个屯上一样。我知道,倒也并非山高路陡之故。山里的孩子,再不济,血脉里面,还延续着先辈的基因。他是想,凹河的桃花开了,李花开了,再有,樱桃红了,桃子熟了,多好!那沉重的一页,还是少想些吧。是啊,把痛苦搁置,向往着美好,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心态?看看那些老辈,或者是老辈的老辈,不就给屯上,取了一个好听的名:画眉! 画眉的叫声好听啊,唧唧唧,咯咯咯,唧唧唧,咯咯咯,“搞快点”“搞快点”,时扬时抑,清丽婉转,一开口,就多姿多彩,像极了凹河的春天。非不怪,它会成为山里人喜欢的灵鹊。由是想,即便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又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内心渴望的愉悦,以及对美好的想往呢?这可能,就是我为凹河山歌一代代的流传,找到的唯一注解。 凹河山歌,兴起于何时,不得而知。也许,第一代落户的先人,就带来了这种文化。顾名思义,山歌山歌,自然是在山上唱的歌。劳作之余,胳膊一伸,腿一张,可劲地来上一嗓,也许,眼前,就出现了相思的小情妹;说不定,那个日也思来夜也想的丫头,正躲在哪个茅草蓬蓬头,巴心巴意地听着呢!这一想,心就哗一下雀跃起来,劳作的苦累,早就飞到了山那边。于是,又狠狠地想,要真有那么几天,可以盘脚四手,陪着心爱的丫头,把太阳唱红,把月亮唱落,那才叫舒坦呀!大家的心思,就这样走到了一起。直到那天,刚过完年三十,出门一走,咦,满山的油菜花,一夜之间,竟然就开了,野天野地,开得放肆,开得迷离。喉咙一痒,情不自禁就张开了口:太阳出来照白岩,金花银花滚下来;金花银花我不爱,只爱情妹好人才。方才落谱,那边,就跟了上来:太阳出来照半坡,金花银花滚下坡;金花银花我不爱,只爱情哥唱山歌……从此,一年一度,每到正月,凹河两岸,就成了两边人的歌场,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 画眉屯的画眉,还在唧唧唧地叫,但凹河的歌场,近些年来,已逐渐式微。也许,是它“俗”而“土”,跟不上“形势”吧。但每年正月,这里,依然还是年轻人的“打卡”地。山歌没有了,但走南闯北的他们,突然又发现,原来,僻远的家乡,竟然是那么美,美的崖,美的水,美的花花,甚至当年那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妹子,就那么一眨眼,仿佛就有了水的清澈,水的灵气。 但我,确实是想听几首山歌的。只为桥边老人那句话:山歌无本,字字是真言。一刹那,脑海里突然就冒出那句话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一想,那时的《诗经》,不就是今天的山歌?只可惜,我可能没这耳福,再听到凹河岸边,那野天野地的歌声了。 戈戈的表达谢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erfenga.com/nefyfyl/6312.html
- 上一篇文章: 最后的木犁牛耕
- 下一篇文章: 宝宝流眼泪ldquo长眼屎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