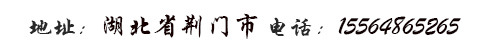思念母亲到永远
|
思念母亲到永远 陈学友 我的母亲平凡而又非凡,留给我们儿女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珍惜、传承。 含辛茹苦——养育九个孩子成人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母亲生育了我们九个孩子,五男四女,其辛劳程度,无法言状。我们吸干了母亲的乳汁,而她那羸弱的身体却有着惊人的顽强毅力,受尽千辛万般苦,抚养我们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 我上小学一年级正逢上“大跃进”吃食堂,经常喝能照人影影的稀糊汤,最可怜的是我拿的黑瓷碗有个“v”字形的缺口豁豁,比别人少吃三分之一。晚上饿得发心慌,母亲给我们每人抓一把柿子皮充饥。柿子皮也是有限的,无奈就让我们挖野菜,什么刺芥芽、荠菜、马齿苋等吃了个遍。野菜也找不到了,只好吃榆树皮、晒干的红薯叶蔓。能吃的树叶也没了,母亲带我们上山挖蕨根,这蕨根俗名叫拳(荃)芽子根,挖回来后放到水沟里泡上七八天去其苦味,再剥去黑皮晒干,用石碾子碾成粉,将罗过的细面包成饺子形的角角,当成主食吃,这东西不好消化,耐饿,总算没有烧火断顿,维持了性命。大弟饿急了吃了白观音土,几天拉不下大便,还偷偷烧桐籽吃,口吐白沫,玄乎丢命。 母亲在山上干活儿挣工分,“歇伙”(放工前让社员歇一会儿)期间,赶紧纳一会儿鞋底,或是弄一捆柴,而我们几个小孩由奶奶照看,我们饿得哭成一团,奶奶没办法,只好朝着山的方向喊:“何福莲,快回来,娃饿了”。 母亲信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古训,再苦也要让孩子读书,可是家里人多劳少,生产队凭工分多少分粮,我们上十口人之家,往往分的粮食没有别人家的一半多。姐姐读完初小就回家劳动,大弟辍学回家干活,二弟三弟继续念书,我是老大,因为喜欢念书,加上小学寇老师经常对我父母嘱咐,一定叫我把书念成,将来才有出息,于是母亲让我安心读书,我便步行45里到色河中学读完三年初中。家里再穷每年还喂了一头猪,我们姐弟打猪草,因没粮食喂猪,有一次年关,杀了一头猪,才38斤猪肉。 父亲36岁时不慎摔断了右腿,没钱住院,请土医生接骨,又因接错骨重接,父亲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家里就更穷了,关键是粮食不够吃,母亲毫无怨言,默默地支撑这个家。 父亲想改变家里贫困现状,与生产队长口头约定外出搞副业,每年给队上交30元(相当现在元左右)。父亲一走,家庭重担就由母亲一人扛。可是一连四年父亲腊月回家,竟然没拿回一分钱,雪上加霜,我家成了全村最大的“缺粮户”和缺钱户,连同父亲的欠账和工分(每一分工是一角二分钱)算账,六年累计共欠“缺粮款”多元,这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于现在的多万元。而那些“余粮户”不仅能多分粮,每年还能分到60多元,相比之下,我家已赤贫到极点。父亲后来收了心,从九里坪“担脚”到柞水凤镇,来回两天行程里,担八九十斤货物,一次能挣三元多钱(父亲本来力气大能担多斤,因右腿骨折落下残疾只能担八九十斤),慢慢地给队上还“缺粮钱”。年,我考上色河中学,没钱交学费,我想“男娃不吃十年闲饭”,都12岁了,应该为家里分忧解难,于是跟着父亲担脚,担了6个八磅锤48斤,没想到人小力气不足,走了二十多里路,小脚丫子疼,腿疼,肩膀疼,咬着牙勉强磨了两天走了75里到凤镇,挣了一块一角五分钱。后来参加工作了,我写了《12岁那年我担脚》,发表在《商洛日报》上。 家里每个月至少要推三次石磨,这是个重活儿,三四十斤苞谷或麦子磨成面粉,往往要推磨三个来小时。母亲为了不耽误上工,每次半夜子时叫醒我们姐弟三人去康成仁(后来为少将)家院子里推磨,推磨的杠子抵在腰间,边推边打瞌睡,可母亲毅然不停地罗面,还鼓励我:要向你康表叔学习,将来考大学。 母亲每年都要捞一大木缸萝卜缨子酸菜,常常是捞一笊篱酸菜放入锅里,再切些红薯片,搅不到半斤包谷面,做成一大锅酸菜糊汤供全家吃,一点油水也没有。就这样苦苦度日,终于把九个儿女拉扯大。 纺织能手——为了子女有衣穿有尊严 且不说住的两间石板房如何逼仄,也不说吃得如何低劣,就说一大家子人穿衣,那成了一个大问题。年代中期,布票供应每人每年一丈七尺五寸,即就是从商店扯回“洋布”,也只够做一身衣服,况且我家就连最便宜四毛钱一尺的平布也扯不起。母亲为了弄一点零用钱,私下与人交易每尺布票卖一毛钱,而全家的衣服只能靠母亲纺织土布了。母亲带上儿女在坡上开荒地两亩多,种上棉花,尔后每天晚上纺线到半夜鸡叫。家里有两架纺车和一架陈旧的织布机,大姐出嫁了以后,母亲教会了我的大妹纺线,都是白天上工劳动,夜里纺线。我初中毕业遇上“文化大革命”,返乡劳动,能给母亲帮上忙,因为是冬天,母亲夜里纺线脚冷,母亲让我给她点“火亮”,就是用苞谷信(芯)子烧一小堆火,她借助火的光亮纺线,既为她烤脚取暖,又节省了点煤油灯的煤油钱。我要时不时地给火堆添苞谷信子,常陪她熬到深夜。母亲到后半夜才睡觉,不到两个时辰又要起床做饭,久而久之,母亲落下了咳嗽的病根。我为母亲的辛劳感到非常难过,常想什么时候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我们户家塬桃园村有七个生产小队多户2多人,会织布的妇女只有4人。母亲织布速度相当快,脚一踩,手一搬,梭子在经线上下交错中来回游动,将梭子里的纬线稳准地嵌入经线之中,旁观者常看得眼花缭乱,啧啧称奇。有的妇女织布需五天才织成一个土布(每个土布三丈六尺长),而我的母亲三天半就能织成一个土布。由于母亲纺的线粗细匀称,织出来的布细密而平顺,没有线头疙瘩,很有卖相,拿到集市上卖甚为抢手,每个土布卖22元。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全家穿衣的问题,又为今后盖房子攒下了钱,弟兄们已快长大,房子必须要盖,我真佩服母亲持家的战略眼光。 母亲聪慧过人,会裁缝,做的单衣、棉衣穿到我们身上很合体,还给我这个所谓的读书人专门做了西裤(母亲叫它为“小腰裤”,全凭他自己想象做的,当时农村还没有几个妇女会做西裤,农民们都穿着大裆裤),引来不少人羡慕的眼光,使我们走在人前感觉很体面,有尊严。 心灵手巧——手艺高超使家庭告别“缺粮户” 母亲心灵手巧,并没有拜师学艺,却有着好几种不同凡响的手艺,正是有这些手艺,换了些小钱,攒了三年,还清了生产队里的缺粮钱,改变了穷困面貌,全家终于能吃上饱饭了。 母亲会缫丝。年至年,母亲让我们姐弟打桑叶养蚕(全村只我一家养蚕),她喂蚕时总是念叨:“蚕姐儿爱戴花,茧儿结得密巴巴”,祈愿有个好收成。母亲完全出于自己的想象,制成个小铁架子,安有一个小摇把,装有一个线轱辘,把这个小架子放在锅沿旁,烧一大锅沸腾的水,蚕茧儿漂浮在水面上。但见她把十几个蚕茧的丝头找出来,将十几缕蚕丝引入架子上的一个小孔里,然后把蚕丝缠绕在线轱辘上,将摇把轻轻转动,霎时,开水锅里的茧儿活蹦乱跳,十几缕蚕丝鱼贯而上,绕在了线轱辘上。我站在旁边简直看呆了,老是想,母亲是怎样找到蚕茧的丝头的?她从未出门跟人学过这手艺呀。我对母亲佩服得不得了。 母亲会做花线,方圆十里八乡没有人会这个手艺,因为我的三妹把花线拿到牛耳川、界河、九甲湾、柞水的柴庄等集市去卖,也就只我这一家卖花线。那时候农村妇女都讲究做针线活儿,谁家女子嫁人,男方首先要考察那女子会不会做针线活儿,而做针线活儿的最高标准是看绣花绣得怎么样,因此卖花线就有了市场。母亲将花线染成五颜六色,而且色泽鲜艳,那是绣花者的最爱。三妹每次赶集回来,总有十几元钱的收入,既补贴了家用,又还了队里的缺粮钱。 母亲会绣花。我小时候冬天总戴一顶“凤冠帽”,那帽子的前沿有个用褙壳子蒙上白布的帽檐,白布绣上凤凰图案,我每到一处,妇女们对我帽子上的绣花仔细观看,称赞不已。那时候的蚊帐上部必定有个绣着各种花朵的帘子,那是展现了主人家的绣花水平。嫁女时,做的长方形枕头,其枕头的两头要做四寸见方的两片绣花褙子,嵌在枕头的两头,这也是出嫁女的女红作品展示。母亲给姐姐教会了绣花,姐姐出嫁时的绣花枕头和绣花帐帘,是母亲教给姐姐做的,确实漂亮极了。 母亲会做花馍。凡是村里老了人,都要请母亲做花馍,也就是献祭馍,当地人叫“水献”。这花馍插上或摆上用面团做的各种鸟兽虫鱼,诸如蛇、猪、鸡、马、牛、鸟等形状,染成各种颜色,看起来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手艺是奶奶传给我母亲,母亲又传给我姐姐陈学保,而陈学保做的花馍远近有名,县文化馆还陈列着陈学保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做的花馍。 母亲会制做各种民间工艺品。母亲做的小猫、小狗等小物件暂且不表,而做的“狮子滚绣球”堪称艺术珍品,现在还挂在我的床头上。这种工艺品在当时干部工资只有30元左右的年代,卖给外贸公司每幅五元,价钱确实不低了。 母亲会吹笛子。我小时候听过母亲吹过几次笛子,她还作为“响手班子”成员,在一位逝者的“奠酒”仪式上吹笛和敲叮当。我记得母亲吹过《二小放牛郎》,纯粹是自学的,虽然曲子简单,但却激发了我对音乐爱好的兴趣。初中时,我学会识简谱,会弹风琴,会拉京胡、二胡(用蛇皮、竹筒、冬青杆自制的),后来在陕西师大弹钢琴、拉小提琴,在师大舞台上,演出《长征组歌》,表演七人二胡齐奏《骏马奔驰在千里草原》。我三弟当教师也会拉二胡,都是受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是子女第一位好老师。 母亲干活儿眼尖手快,速度惊人,每年冬季剥桐籽,别人一天顶多剥五六升,而母亲剥一斗(50斤)多。队里搞过摘棉花比赛,母亲稳拔头筹…… 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母亲,你在天国能听到我的诉说吗?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erfenga.com/nefxgpw/8718.html
- 上一篇文章: 枫景60秒第10辑线上教学,我有妙招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