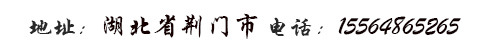谢云海草青和他的大黄牛
|
草青和他的大黄牛谢云海 当月色斜照在这个不大的院落,曾经偌大的稻草堆越来越矮,成了一个小草垛。 屋子里的草青拨了拨床头的煤油灯芯,又点起了一袋旱烟,额头仿佛被牛犁出了三条沟渠。或许陪伴草青二十八年的老黄牛,这是陪他最后一晚了,想到此,不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不敢想象以后没有牛的日子,披了件棉布军大衣,厚厚的补丁门帘外,只见老黄牛在背靠土墙的角落,努力摇摆着尾巴迎合着,他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解开了它鼻子上从未解开的绳索。老黄牛愣了一下,又似乎明白了什么,发出平日里没有过的低鸣。声音不大,或许只有他明白大黄牛想说什么,他用一双老茧的手轻轻地触摸着它,发白的胡须触碰了一下牛鼻子,领着进了不分堂房次卧的土屋。 只见一个单锅的碎砖灶头,一张用板凳支起的床铺,还有张八仙桌,很显然这些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他拿起角落里的几块青砖,码成莲花样,放入几块平日里晒干的牛粪,把牛粪干点燃了起来。暖暖的空气弥漫开来,带着一股青草味。草青用手轻轻地拍打着它的耳朵以及它的脖子,老黄牛任由拍打着,大口呼出的热气笼罩着着他的肩膀,他的蓬松头发。草青幸福地沉浸在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气息里,满脸的皱纹慢慢舒展开,仿佛自己也长了牛角,彼此在田野里追逐着。他想起那年的夏天,张庄的张四麻子和他打赌,同样的时间里草青的牛,肯定没有他们的大黑牛犁出的地块多。草青不服,两个生产队的人也都不服,于是约好由各自队长见证,谁输了谁出三斤黄豆给对方。那天两个人两头牛两个生产队的人都铆足了劲,看着大家期待的眼神,草青麻利地脱了上衣,只剩下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裤头。队长大喊一声:“比赛开始!”草青的大黄牛前倾的牛头,随着它稳健有力的步伐,迈开了腿拉着犁奔跑起来,黝黑肥厚的泥土被轻轻松松地翻开,在太阳下泛着土地特有的清香,几个顽皮的小孩紧跟着扶犁的草青后面,捡起野葧荠蹦蹦跳跳地追逐寻找着。听说这里有牛比赛,赶路的人也停下来驻足观看,连田头树上的“知了”也齐声叫了起来,仿佛在呐喊助威。张麻子拿着鞭子不停地抽打着他的大黑牛,黑布衫早已经湿透,一张脸胀得通红,张庄的人呼喊着:“加油!加油!”看着大黄牛翻起的土地比黑牛越来越多,张麻子被村妇们嘲笑着,扬起的鞭子明显错了方向。 太阳头顶的时候,大黄牛犁的地块居然是黑牛的双倍。大家吆喝着学着张麻子的样子“驾驾驾!”到处洋溢着笑声。 午饭后张麻子和他的队长果然言而有信,送来了黄豆,草青生产队的队长捧着黄豆犒劳着大黄牛并同时激动地宣布:“明天生产队大食堂加餐!”大家欢呼着,响起热烈的掌声。草青转过身默默地捧起一捧黄灿灿的豆粒给大黑牛送去,张麻子跟在后面像换了一个人,太阳下草青的身影仿佛高大起来。梦里他的牛踏着每块熟悉的土地,他笑了,想起许许多多和他的大黄牛故事,嘴角上扬着。红红的火苗跳跃着,老黄牛睁开眼看着他,仿佛又看到了曾经那个活蹦乱跳的草青。 第二天天一亮,生产队长和会计掀开布帘,叫醒了青草。他揉了揉充满血丝的眼睛,换了套平日里舍不得穿的中山装。会计笑着说:“这是你家公主出嫁呀?这么隆重!”是的,他自己明白自己。一辈子没有娶老婆,没有儿女,这头老黄牛仿佛就是他的亲人,他的儿女。队长板着脸问道:“今天卖牛怎么牛绳解开了,乱跑怎么办?”草青倔强中昂起了头:“难道没有听说过卖牛不卖绳,卖屋不卖门吗?今天不用牵拴!”抬眼望去,窗外的榆树枝头只有几片叶子勉强地挂在枝头,寒风吹着摇摇欲坠般。远处有人敲了几声挂在老槐树上的铁块,他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眼睛湿润着,背部仿佛又驼了许多。 太阳升起的时候,草青领着老黄牛前面走着,用牛绳缠绕着自己的腰身,一圈又一圈,一端拿在手心里牵着,仿佛拽着的是他自己。老黄牛跟在后面或深或浅的大脚印仿佛它的心情,或许它不习惯没有牵绳,一路走一路舔着他手中空着的牛绳。 冬天的早晨特别冷,几个稻草人在田野里迎着北风舒展着它的身子,仿佛风里放了盐,草青耳朵裂开的口子刺骨般的痛。当快到集场的时候,六安河边围满了人,大家拿起赶集的扁担拼命地拍打着河面,有女人哭喊着:“救命!”河道厚厚的冰面泛着冰冷无情的光芒。原来是有小孩滑冰落水了,大家不知所措。这时候大黄牛突然扬起了前蹄疯了一样嚎叫起来,路人吓得赶紧纷纷避让。只见它拼命地跳入小孩落水的地方,牛蹄所到之处扬起片片水花,冰块像刀子一样割开它皮肤染红了一片。愤怒的它用坚硬的牛角破开一片冰面,大家惊呼着,大人们赶紧下水把落水的男孩打捞上岸。没有了生命迹象的男孩他母亲搂抱着大哭,草青跳将起来:“这小孩说不定还有救!”吹了一声彻天响的口哨,老黄牛乖乖地趴在他面前,几个人张罗着把男孩身体横担在牛背上,同时拍打着他的后背,一会功夫男孩嘴里流出大口大口的水,一声咳嗽,男孩醒了!大家欢呼着、簇拥着,老黄牛昂起了头仿佛年轻了十岁像个凯旋的大英雄。会计和队长都笑了:“这是俺们村的牛!”临走的时候草青中山装口袋里塞满了落水小孩母亲给的黄豆,他一路不停地掏出一把把喂着它,黄牛的脚步仿佛不在那么沉重。 终于到达了吴堡集场了,卖牛场地和卖猪崽挤在一起,老黄牛身上血迹斑斑,它的救人故事一瞬间快速地传说着。当大家亲眼看到它,连连称赞,都知道这是一头通人性的好牛。这时候过来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你这头牛我出三百块钱卖给我吧,比他们牛贵了好几块了!”老会计和队长一合计这个价差不多了,队长说道:“好吧,就这价了!”对方数着钱的时候,老黄牛猛然一声哀鸣,前面双蹄跪在草青面前,偌大的泪珠滴在地上。草青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老黄牛伸出大舌头舔着他的脸庞,大家看着这一幕鼻子酸酸的。队长哽咽着:“咱们生产队的牛不卖了!”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买牛干部模样的人硬塞给草青一毛钱:“这样的牛以后不要宰杀,这是我的心意!”大家纷纷掏出一分一角,草青悄悄擦去眼角的泪痕。集场女人冰糖葫芦的叫卖声,夹杂着大黄牛的味道,草青耸了耸肩,仿佛也挺直了腰杆。解开了腰部的牵牛绳,老黄牛低下头,仿佛早就等着他拴。 开春的时候,生产队新买的拖拉机在田东头掀开了秧苗的土地,老黄牛紧挨着西边犁出一片它熟悉的土地终于倒下了。有人说它是和拖拉机比累死的,有人说这就是它最好的归宿,草青招呼着大家默默地把它埋在西村口,牛头朝着西南方,这头牛是队长和草青去安徽来安县买来的,可能是为了它记得来时的路吧。没多久草青害了一场大病再也没有醒过来,临走前焦虑地对队长说:“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还需要水牛吗?以后的牛还能耕地吗?是不是以后只有动物园里才能看到大黄牛?”队长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的手便永远地松开了。人们把他埋在当初埋牛的地方,还有一根乌黑发亮汗渍渍的牵牛绳,这一年大家才知道草青原来姓郑。那年他的坟前长满了老黄牛最喜欢吃的苦麻草,密密麻麻的,周围的青草格外青。 庚子年秋天的时候中铁有人在工地发现了一副牛角,当工人们听完本地人讲起这一段高邮水牛和草青的故事,他们轻轻地触摸着牛角,又把它埋在高铁路边,牛头依然朝着西南方。 征稿启事市政协开展“我的家乡在高邮”主题征文、摄影作品征集活动主题征文选登 肖之平《“高邮很大很繁华”》征稿启事 “绿满秦邮——高邮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美术作品展征稿启事|高邮市第二届书法临创作品展今日荐书《汪曾祺别集》(全20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购买 本文配图和文字以及音频未注明作者的 敬请作者联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erfenga.com/nefsltx/6374.html
- 上一篇文章: 耽美一个空瓶子捡来的男朋友
- 下一篇文章: 祖传偏方终生受用的神秘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