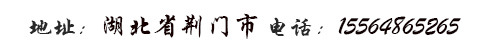木舍手记蓼草花之秋
|
北京哪家医院看白癜风专业 https://4001582233.114.qq.com/ 今日秋分,刮在田野上空的风已有了兵气。 清晨六点半至浦溪河,见河面水雾凝聚,团团簇簇。节气这东西真是奇妙,一日之隔,自然界的物象就有了明显变化。 半个月没下雨,河水退下不少,河中间的浅滩上,野花汀草茂密,成为潜鸟的隐身地和繁衍后代的乐园。 生在河滩的野花我认得,是蓼草花,早些年在散文里就写过,称之为辣蓼——以为只有我们本地方言这样称呼,后来才知它在《本草纲目》里也是这个名字。 不是所有的蓼草都叫辣蓼。辣蓼只是蓼草的一种。走到它们中间,仔细看就会发现,同是蓼草,仅从颜色上就能分出五六款来,粉红、紫红、朱红、粉白、青白,还有几种颜色相杂的。 要分清植物的名字是很麻烦的事,能把人弄得晕头转向。我可不想在这上面钻牛角尖。对于蓼草,我有自己的区分法——生在田间的就叫田蓼,生在河滩的就叫水蓼,朱红的叫红蓼,白色的叫白蓼,采下来时在指尖留下辛辣味的叫辣蓼,留下辛香味的叫香蓼。 小时候,夏末秋初会采辣蓼来驱蚊虫,挑那有些老的粗壮的,齐根割下。将采来的辣蓼晒上一个日头,捆成一小把一小把,天黑之前,点一把放在脚边,让烟淡淡地飘着,蚊虫就不敢近身了。辣蓼散发的野生气息微微地呛人,又有股子爽朗劲儿,闻到这味道就会想到“泼辣”这个词,想到“疾风知劲草”的秋日旷野。 小时候对于植物的认识是物质的,要么吃,要么用。对它们审美性的感受是成年后的事——准确地说,是开始写作自然笔记之后的事。 自然笔记的写作,促使我对原先熟悉的事物重新去认识、审视,像一个从远方回来的人,重新辨认眼前的一草一木,去闻,去听,去触摸。当一个人用写作的方式,再一次认识和感受这个世界,就是从这个世界——从一草一木之中——甚至是从一株被阳光照得金灿的狗尾巴草里,重新让自己诞生。 蓼草花对我来说就是秋季的象征。整个秋天,我都是用蓼草花来插瓶,放在书架前和茶几上。起先是从田边采来满天星状的田蓼,之后采的是垂穗状红蓼,再后来就是辣蓼、香蓼,或将几种颜色的蓼草混合在一起,让它们在一只旧陶瓶里“小团圆”。 蓼草的花期很长,从稻禾扬花开到稻禾成熟、收割,直到霜降时仍在开。此时田野里几乎看不到别的草花了,要么结了籽,要么被带着兵刃气息的风吹得金黄、干枯,伏在地上,等待着泥土的吸收。 蓼草是群居植物。当它还是草时,你看不到它,当它开花时,就见出气势了,一开一大片。由此也可见它们的生命力,是强韧到带有侵略性的——这也是野草的共性。 河滩里的水蓼也是聚族生长,毫不客气地占满整片汀渚。 一条开满水蓼花的河就是流花的河了。当带着水晶质感的秋阳照在河心,将水蓼的倒影投在水面时,很容易就想起《红楼梦》里的“蓼汀花溆”四个字。美妙的是,从这蓼汀里又时不时地飞出白鹭、斑嘴鸭,或游出秧鸡、黑水鸭,或者在你路过时,从蓼汀深处传来让人心里莫名发愁,然而又很温暖的呼唤——仿佛那是一个从前的伙伴在叫着你的名字,你回头寻找,却看不见那人。 项丽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erfenga.com/nefpzff/4314.html
- 上一篇文章: 此草辣味不输辣椒,农民用它做酒曲,20年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